
去年秋天,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將滿一年之際,《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主編Wen Huang前往歐洲親身觀察這場人道危機。在他分兩期之報導的第二部分,Wen Huang造訪利沃夫(Lviv),在此他見證了烏克蘭人民的韌性及扶輪全球網絡的無所不在。
星期五上午10時,波蘭東南部
───────────────────
仍帶著男孩氣質的波隆斯基(Vasyl Polonskyy)露出大大微笑驚呼道:「我現在可以聞到烏克蘭的氣味了。我們非常靠近邊境了。」
我們沿著一條新鋪設的鄉村道路穿越波蘭東南部。波隆斯基把頭伸出窗外,深深吸了一口氣。我也跟著這麼做,但是沒有聞到任何明顯與烏克蘭有關的味道。波隆斯基看出我的想法。他說:「只有烏克蘭人能夠察覺我們國土的獨特氣味。每次我從國外返國,一向只要靠氣味就知道我回國了。我熱愛我的國家,這場戰爭只是讓我的愛更濃烈而已。」
今天稍早我在波蘭小鎮札莫希奇(Zamość)與波隆斯基會合。身材修長的他是烏克蘭團結護照(Ukraine Unity Passport)扶輪社的社長當選人。他與利沃夫扶輪社社員、前2232地區(包括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總監亨納迪‧克羅伊奇(Hennadii Kroichyk)破曉就起床,開車橫越邊境來載我及艾德‧瑟寇(Ed Zirkle),後者是俄亥俄州哥倫布(Columbus)扶輪社社員,是一位專業攝影師。
在俄羅斯入侵之後,烏克蘭政府禁止大多數60歲以下的男性出國,以便受徵召入伍。我問波隆斯基他的服役狀態。他回答說:「還沒。我用不同的方式來幫助我的國家。」他與其他扶輪成員有特殊通行證,一個月開車進入波蘭好幾次來匯集世界各地扶輪社所捐獻的食物、藥品、衣物,及發電機;他們安排把這些必需品分配到烏克蘭各地受創最嚴重的城市。就在我造訪前不久,他們才前往波蘭去接紐澤西州梅德佛晨間(Medford Sunrise)扶輪社社員所捐獻並從德國開到波蘭的救護車(共2輛,此趟為第2輛)。他們最近也搭乘一輛小型巴士返國,上頭裝滿芬蘭扶輪社員捐贈的醫療用品。
在此之前一直默默坐在汽車後座的克羅伊奇說:「在這樣的時刻,扶輪網絡真的顯得很驚人。」
 當我們接近波蘭邊境時,我們經過一長列的卡車。克羅伊奇說排隊的車陣可能長達2或3英里,駕駛有時候必須等好幾天才能通過邊境關卡。所幸,小客車的隊伍很短―― 戰爭已經讓觀光業全面陣亡。我和瑟寇想要拍攝我們入境的瞬間,可是波隆斯基阻止我們。他警告說:「如果衛兵懷疑你是媒體人士,他們可能會把我們拉到一旁盤查。」
當我們接近波蘭邊境時,我們經過一長列的卡車。克羅伊奇說排隊的車陣可能長達2或3英里,駕駛有時候必須等好幾天才能通過邊境關卡。所幸,小客車的隊伍很短―― 戰爭已經讓觀光業全面陣亡。我和瑟寇想要拍攝我們入境的瞬間,可是波隆斯基阻止我們。他警告說:「如果衛兵懷疑你是媒體人士,他們可能會把我們拉到一旁盤查。」在邊境的崗哨,波隆斯基告訴官員我及瑟寇是美國來的平民義工。不用幾分鐘,我的護照多了兩個簽證戳章。
我們即將進入戰爭國家的念頭讓我此行露出明顯的緊張,可是不安的感覺在邊境時卻轉變為興奮。我拍攝一個標示到利沃夫及基輔之距離的巨大藍色告示牌,並把照片傳給我在美國的朋友看,附上一則歡樂的訊息:「我剛剛進入烏克蘭。」
星期五中午,接近利沃夫
────────────────
波隆斯基宣布:「我們離我的家鄉利沃夫市67公里。」他戴上一副飛行員太陽眼鏡。「回家的感覺真好。」
在我們前方的是一望無際的翠綠農地。瑟寇說:「如果不是有烏克蘭文的路標,我們很可能像是開在俄亥俄州或伊利諾州。」
克羅伊奇插話說:「我們有黑土,非常肥沃。隨便種什麼都會長。」
波隆斯基說:「烏克蘭是世界糧倉之一。我們的穀物出口到歐洲、非洲及亞洲。」他說俄羅斯總統普丁重現史達林的戰術,破壞烏克蘭的各項產業及農業,同時讓人民挨餓受凍來迫使其屈服,企圖摧毀這個自由的國度。
利沃夫一帶向來是數百萬烏克蘭人—多數是女性、兒童,及較年長者―― 逃離該國的通道。在我造訪期間,這個烏克蘭西部的大都市大體上逃過俄羅斯的轟炸及飛彈攻擊,雖然更近期對該市電力網的破壞攻擊讓冬天十分難捱。
然而,在通往利沃夫的鄉村道路上生活顯得很正常。我們經過有紅色屋頂的農舍,看到農夫在田裡工作。偶爾,我看到教堂的圓頂。這個祥和的景象讓我漸漸進入夢鄉。
車子突然急停。醒來時我發現一名士兵往車窗裡查看。我們在一個軍事檢查哨。沙袋及水泥塊阻擋部分道路,更遠處有稱為「刺蝟」的金屬反坦克路障。它們明白提醒我們身在戰區。我的焦慮回來了。
在盤查後,波隆斯基關上車窗,宣布我們抵達利沃夫。再次,他警告在我們到旅館的路上不要拍攝有衛兵駐守的橋梁或檢查哨。人們可能會懷疑我們是dyversanti―― 試圖把可能目標通報給俄羅斯人的破壞分子。
我們開車經過購物中心時,我很驚訝看到有一個新的建築工地掛著七彩的廣告看板,宣傳一個美麗的住宅社區。從戰爭開始,波隆斯基說超過15萬名流離失所的烏克蘭人已經定居在利沃夫。該市正在興建公寓來收容他們。克羅伊奇說:「大家盡可能讓生活維持正常。」
星期五下午3時,利沃夫飯店
──────────────────
鋪著假大理石地板的利沃夫飯店(Lviv Hotel)大廳是蘇聯時期實用主義的產物。可是在我環目四望之際,在一個老式的電梯門口看到一個熟悉的旗幟,上頭用大大的紫色字母寫著Imagine Rotary(想像扶輪)—國際扶輪社長珍妮佛‧瓊斯的主題。我突然間有身在主場的感覺。
當你在地球另一端的飯店辦理入住手續時,你通常會被告知餐廳、健身房,及酒吧的位置。可是在利沃夫,嚴肅的年輕接待人員告訴我防空避難所的路線。我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我的房間有電,但水龍頭流出的熱水卻是涓涓細流。然而在長途跋涉後這已經讓我心懷感激。一小時後,我與其他約50位扶輪社員擠在飯店二樓一間小小的會議室。他們來這裡參加一場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烏克蘭的扶輪區域雜誌出版人米科拉‧斯特布爾揚科(Mykola Stebljanko)正在做簡報。一個星期前,我在柏林渡假時,斯特布爾揚科邀請我參加這個研習會,讓我大感意外。此後,我的假期就一直在往東走,遵循一位帶著英國口音、名叫柏里斯‧波德納(Borys Bodnar)的神祕人物在電話中的指示。
在休息後,那個帶著口音的熟悉聲音從我背後傳來。「柏里斯。」我脫口而出並轉身過去。這位詳細指示我烏克蘭之行每段路程的神祕男子結果是一位英俊高大的人。我問他的英國口音從哪來。
他解釋說,他的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逃離烏克蘭,落腳英國。他出生在雷瑟斯特(Leicester),在倫敦度過大半輩子,在不同金融機構擔任稅務顧問及稽核,可是他4年前來到利沃夫。他表示,他開了一家辦公家具出口公司,並與扶輪連結來「認識更多人,結果變得投入行善工作。」2020年6月,波德納成為烏克蘭團結護照扶輪社的創社社長。他說:「在成立扶輪社不到6個星期,我們就有35名社員加入。現在我們有37位社員。大家都想要加入我們,一起幫忙。」
 波德納說,戰爭開打時,烏克蘭的扶輪社員組成一個危機委員會。他們的優先事項之一就是協助逃離被攻擊城市的難民。波德納解釋說:「我們歡迎難民,提供他們過正常生活的機會,直到這場浩劫結束。在非常艱困的情況下,我們盡全力幫助他們穿越國界,確保外面的扶輪網絡可以協助讓他們感到安全。」
波德納說,戰爭開打時,烏克蘭的扶輪社員組成一個危機委員會。他們的優先事項之一就是協助逃離被攻擊城市的難民。波德納解釋說:「我們歡迎難民,提供他們過正常生活的機會,直到這場浩劫結束。在非常艱困的情況下,我們盡全力幫助他們穿越國界,確保外面的扶輪網絡可以協助讓他們感到安全。」戰爭中斷波德納的事業;目前,扶輪成為他全年無休的工作。他說:「我隨時待命,與世界各地的地區及扶輪社聯繫。我也協助規劃運送捐贈物資的後勤工作。」危機委員會確保世界各地扶輪社所捐贈的那些物資都能夠分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波德納給我看一包淨水錠。在扶輪基金會的協助之下,烏克蘭團結護照扶輪社與英國、愛爾蘭,及美國的扶輪社已經購買這些淨水錠給前線區域乾淨水源遭破壞的家庭。同時,波德納的扶輪社正在與英國扶輪社所創立的慈善組織「水箱」(Aquabox)及「水存活箱」(Water Survival Box)合作,取得濾水組送到烏克蘭分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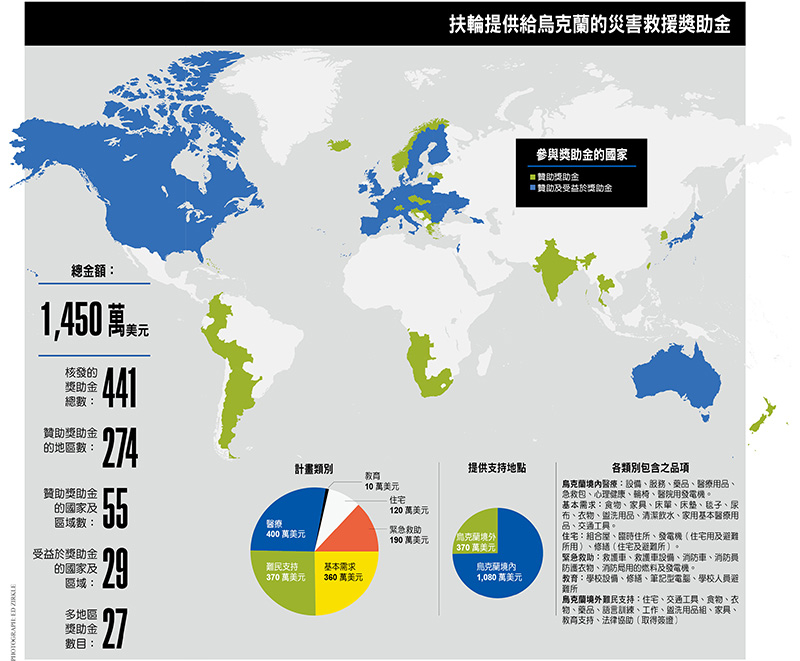
 一位留鬍子的年輕男子加入我們的對話。兩個月前,賽吉‧費多托夫(Sergii Fedotov)因為想要出一分力,加入哈爾科夫新水平(Kharkiv New Level)扶輪社。生性樂觀的他已經在談戰後重建烏克蘭的事。費多托夫努力用英文表達。他說:「幫助他人讓我感覺我的靈魂在昇華,我的微笑越來越大。」
一位留鬍子的年輕男子加入我們的對話。兩個月前,賽吉‧費多托夫(Sergii Fedotov)因為想要出一分力,加入哈爾科夫新水平(Kharkiv New Level)扶輪社。生性樂觀的他已經在談戰後重建烏克蘭的事。費多托夫努力用英文表達。他說:「幫助他人讓我感覺我的靈魂在昇華,我的微笑越來越大。」費多托夫的社友愛琳娜‧伊凡諾娃(Iryna Ivanova)分享她的故事。她與同是扶輪社員的夫婿韓納迪(Hennadii)在3月份俄羅斯轟炸哈爾科夫後,帶著4個孩子逃離該市。在漫長、迂迴的旅程之後,他們抵達都柏林。雖然他們已獲得愛爾蘭人收容,伊凡諾娃不曾忘記她的家園。在扶輪研習會中,她希望與扶輪網絡重新連結,確保哈爾科夫的人可以獲得必要的物資以度過酷寒的冬天。
伊凡諾娃驕傲地告訴我哈爾科夫8個扶輪社如何在一個扶輪社員管理的購物中心外,興建一座大型的倉庫。扶輪社員在那裡收集、裝載,及分發扶輪及歐洲與北美洲各種救災機構所捐贈的物資。每天有50餘位志工從事物資的分類及分送工作。她說:「戰前,許多人―― 包括一些扶輪成員—很可能都不瞭解扶輪的力量。現在,當他們看到扶輪社員如何協助他人,他們會想要加入扶輪。」
星期五下午5時,利沃夫飯店
──────────────────
空襲警報重重敲擊我的耳膜。短暫驚慌後,我跑回我的房間。我抓起我的筆電、皮夾,及手機充電器,衝下樓梯到大廳。一片空蕩蕩。
摸索著走到地下室,我看到4個年輕人圍成圓圈坐在椅子上,在手機上打字。兩個較年長的人用烏克蘭語聊著好笑的事。沒有人顯得害怕。我用英語問:「你們知道大家在哪裡嗎?」他們看著我,面露疑惑。
我上樓走到街上。人們隨意做著自己的事。回到飯店大廳,我遇到哈爾科夫-納迪亞(Kharkiv Nadiya)扶輪社社長尤莉雅‧帕維申科(Iuliia Pavichenko)。她解釋說Nadiya在烏克蘭文表示「希望」。
「你聽聽警報聲。」我大叫。「大家怎麼可以這麼冷靜不害怕?」
她用帶著口音的英語回答:「這是個全國性的空襲警報,不是針對利沃夫。(戰爭剛開始時)我們會害怕,快速跑到避難所。可是我們知道生活還是要過下去,我們必須對抗俄羅斯人。我們不可以害怕。」
我們在長沙發上坐下來。帕維申科給我看她家的照片,天花板被炸毀。她不會一直沉湎於這件事。相反地,她渴望告訴我一項提供兒童及其家人心理支援的扶輪社計畫,別名為「烏克蘭的健康未來」。她說:「烏克蘭兒童在戰爭中遭受很大的痛苦。許多人被迫離開家裡,與家人分隔兩地。他們的父親入伍,祖父母已經逃到其他城市。那便是我們決定幫助他們的原因。」
10月初,她的扶輪社連同烏日霍羅德(Uzhgorod)扶輪社、烏日霍羅德-史卡拉(Uzhgorod-Skala)扶輪社、拉克赫夫-歐洲中心(Rakhiv-Center of Europe)扶輪社、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Ivano-Frankivsk)扶輪社、及羅夫諾(Rivne)扶輪社,與芬蘭的羅瓦涅米聖誕老人(Rovaniemi Santa Claus)扶輪社合作,主辦一項聖誕老人特別活動。來自拉普蘭(Lapland)的一位聖誕老人造訪多個烏克蘭城市。兒童―― 包括孤兒及被迫離開家園的兒童―― 熱烈歡迎他。
帕維申科解釋說:「我們請孩子寫信給聖誕老人談論他們的夢想,並畫出他們的夢想。」她滑著她的iPad,給我看聖誕老人與孩子的合影。「在聖誕老人造訪期間,他們獻上他們的信及圖畫。那是個很美好的經驗。它會留在他們的記憶中很久很久。」

在某個城市,俄羅斯飛彈讓聖誕老人連忙躲進防空避難所,可是並沒有終止他的拜訪。帕維申科說:「我們勇敢的朋友讓我們引以為榮,我們感謝他的扶輪服務。」
星期五晚上8時半,舊城
───────────────
中古時代及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外牆燈光昏暗—考慮到這座城市被轟炸摧殘的電力網乃是必要之舉――大多數的窗戶外都以木板遮光,可是今晚在利沃夫國家歌劇院(Lviv National Opera)前的巨大廣場卻很熱鬧。米科拉及奧爾嘉‧斯特布爾揚科(Olga Stebljanko)――烏克蘭網路扶輪社的夫妻檔社員―― 帶我出來看看這座城市的夜生活。我們散步穿越舊城區,這裡是利沃夫歷史悠久的市中心,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一大群年輕人聚集在一位唱著一首感傷烏克蘭歌曲的街頭歌手四周,歌詞描述一位母親悲悼戰死沙場的兒子。大約50英尺(約15公尺)外,大學生模樣的人牽著手圍著大圈圈,配合吉他手彈奏的活潑曲調開心跳舞。
我說:「一切看起來是這麼不切實際但同時又再正常不過。」可是在斯特布爾揚科夫婦回答前,我便看到一個驚人的證據,證明這裡沒有什麼是正常的。在街邊停著幾輛遭焚毀的俄羅斯坦克,輪子都變形,一部分還熔化。附近一個告示牌顯示它們是在基輔近郊的戰役中被摧毀。
我們進入聖彼得和保祿駐軍教堂(Saints Peter and Paul Garrison Church),這座巴洛克建築有色彩繽紛之壁畫裝飾的圓頂天花板。因為現在這座教堂歸烏克蘭東正教教會的軍隊牧師所管轄,人們到這裡來懸掛陣亡者的照片:烏克蘭士兵,不分老少,一年前還是農夫、商人、或工匠。我屏住呼吸。在走道間也有烏克蘭戰爭孤兒的照片―― 他們的父親於戰爭中身亡。
在高聳的拱門下,2名穿著黑衣的女子跪地祈禱。其中一位在啜泣。看到她的痛苦讓我無法動彈。我僵硬地慢慢走離教堂,試著理解戰爭對無辜者造成的衝擊。
等到我們在一間點著蠟燭的餐廳坐下來時,離宵禁只剩下一小時。米科拉叫喊著說:「在烏克蘭,一定要喝horilka。」然後他點了一排色彩繽紛的試管,裡頭裝著各種烏克蘭伏特加。我回答:「我很需要喝。」即使我平常很少喝酒。
生在哈爾科夫一帶、現年49歲的米科拉在克里米亞長大。2014年俄羅斯佔領該地後,生活變得很困難。他說:「在公共場所我們再也不能侃侃而談,因為可能會有人向當局舉報我們。俄羅斯情報官員試圖滲透我的扶輪社。」這個危急的情況促使他及奧爾嘉賣了房子,搬到烏克蘭西南部的奧德薩(Odesa)。
過去一年來,隨著戰爭持續肆虐,米科拉讓自己成為烏克蘭扶輪社員及美國的國際扶輪世界總部之間的橋梁。我每個星期透過視訊電話與他交談。他很少談到自己個人的情況,可是有一天我逼問他,他說奧德薩正在承受頻繁的火箭攻擊,奧爾嘉和他們的愛犬Yurasik有時候必須一起蜷縮在浴室,那是他們公寓裡最安全的地方。
然而,這對夫妻還是抱持樂觀。當我問到他是否考慮離開烏克蘭,他回答說:「不會,這裡是我的家,我想要留下來幫忙。」他提醒我說他的名字米科拉――相當於烏克蘭文的Nicholas ――意思是「人民的勝利」。
奧爾嘉舉杯說:「克里米亞及烏克蘭人民的勝利。」
星期六下午2時,利沃夫國家歌劇院
──────────────────────
 我們回到歌劇院來慶祝利沃夫扶輪社成立30週年,雖然說基本上應該算是慶祝該社復社。該社原創立於1935年,是該市第一個扶輪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解散;現在的社是1992年重新加盟。
我們回到歌劇院來慶祝利沃夫扶輪社成立30週年,雖然說基本上應該算是慶祝該社復社。該社原創立於1935年,是該市第一個扶輪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解散;現在的社是1992年重新加盟。演講者包括2232地區總監維塔利‧雷斯科(Vitalii Lesko)。雷斯科以前經營一間公關公司,可是在俄羅斯入侵第一天他就到募兵辦公室報到,排隊等了約6小時。他告訴我:「我沒受過軍事訓練,不曾接觸過武器。」他被拒絕了。隔天早上,天還沒亮他又去排隊;受到他愛國心感動的軍官把他分配到烏克蘭西北部羅夫諾區域一個領土保衛志工營。
我也跟賽吉‧薩瓦德斯基(Sergii Zavadskyi)談話,他也是2232地區前總監,基輔-城市(Kyiv-City)扶輪社社員。他熱切告訴我扶輪在莫遜(Moshchun)所做的事。這裡原是基輔市郊一個風景如畫的村落,但幾乎被俄羅斯軍隊夷為平地。至少有70%的房舍遭破壞或摧毀,許多平民喪生或受傷。

薩瓦德斯基的社與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扶輪社及慈善組織「烏克蘭夢想」(UA Dream)合作,建立莫遜重建計畫。基輔-蘇菲亞(Kyiv-Sophia)扶輪社也加入他們的行列,並獲得扶輪基金會災害救援獎助金及其他數個國家扶輪社及地區捐款的協助。他們的目標:清除莫遜的殘骸,並搭建300間組合屋。
第一間組合屋在6月完成,屋主是露柏夫‧托波爾(Lyubov Topol),之前一顆炸彈落在她家旁邊,讓她失去住家及兒子。很快,更多給托波爾鄰居及莫遜村其他家庭的組合屋也運抵。薩瓦德斯基滑動手機上的照片說:「我們努力復原這座古老的村莊,提供當地居民最起碼的生活,包括牆壁、暖氣、頭上有個
屋頂。」
星期天清晨6時,再見
──────────────
天還沒亮,波德那及波隆斯基就開車來利沃夫飯店接我,要送我到波蘭的熱舒夫(Rzeszów)。從那裡,我要搭機到華沙,然後再到柏林。
前一天下午,這兩名男子開車載我經過利沃夫的鵝卵石街道,抵達一間儲藏來自世界各地捐贈物資的倉庫。波德納說:「我們的扶輪網絡讓我們能夠把這些物資運送到很難抵達的前線城鎮。我們預計下星期德國萊茵河畔英格爾海姆(Ingelheim am Rhein)扶輪社及美茵茲(Mainz)扶輪社捐獻的第三批醫療用品抵達後,倉庫就會滿。」
可是波隆斯基補充說:「我們還是需要扶輪的持續協助。」我當時不知道,這位年輕男子的母親不久前被診斷出癌症。她在聖誕節前夕往生。
波蘭邊境的排隊隊伍很長。等到海關官員徹底檢查我的護照及行李後,已經中午了。在熱舒夫,我們道別前,波德拉比了一下烏克蘭獨立運動年代所使用的3指禮。然後他複述2個月前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所說的話:「我們以前講『和平』。現在我們說『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