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MAIKA ELAN
越南胡志明市屢獲殊榮的攝影師Maika Elan於2016 年在日本千葉製作了這分關於繭居族現象的相片紀錄。
2017年,在吉村功大(音譯)離開他鄰近日本海的安靜家鄉前往繁華的大阪之後,他的心態開始慢慢轉變。
他在關西大學的大一生活理應是一段充滿新體驗及新友誼的時光。然而,吉村發現他對讀書失去興趣。他開始蹺課,窩在他公寓的時間越來越長,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流逝,他黏在PlayStation 4遊戲機前,往往熬夜到凌晨3時。
隨著《決勝時刻》(Call of Duty)等第一人稱射擊遊戲消耗掉他許多日日夜夜,他開始躲避他人,儘可能避免出入公共場所。不到幾個月,他已經成為繭居族,一位躲避社交的人士。26歲的吉村回憶那些蟄居的日子時說:「並不是我遭受霸凌之類的。我只是不想看到其他同學。」可是,不久後,他就在一個不尋常的地方找到援助,在幾個月的時間裡讓他的人生產生大逆轉。
繭居族通常被定義為把自己孤立在家裡超過6個月以上的人,鮮少與家人以外的人互動,有時候則是完全不與人互動。這個詞語可以指經歷這種極端孤立狀態的人或是這個現象本身,最常被觀察到的地方便是日本。過去20年來,隨著案例數目成長,這個現象在日本已經成為越來越引人擔憂的公共議題,雖然人數仍僅佔總人口極小的比例而已。可是自2020年起新冠疫情讓人數暴增後,這種擔憂顯得益發急迫。
最近一項政府調查發現,日本經歷過繭居的勞動年齡人口有20%說新冠疫情是他們社交孤立的因素。《繭居青春:從拒學到社會退縮的探討與治療》(Hikikomori: Adolescence Without End)一書的作者,大學心理學家齋藤環告訴《日經Gooday》(Nikkei Gooday)網路雜誌說:「長期繭居的問題光是靠個人及家人的自助努力就能獲得解決的情況極為罕見。」
許多組織出現了—— 有些由前繭居者經營 —— 來幫助人們重新融入社會。這個過程很棘手,很辛苦,有時會花上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的時間。可是這個經驗可以讓人改頭換面。
日本的繭居族常常把自己與世隔絕,躲避他人,把自己沉浸在「宅」(用來表示狂粉的日本用語)的世界,沉迷於電動、動畫、漫畫,或其他一些流行文化的休閒。
雖然很多重點是放在青少年及年輕成人上,估計有150萬名勞動年齡的日本人(總人口1億2,500萬)經歷過繭居。根據日本內閣府2023年一項隨機挑選1萬1,300人所做的問卷調查,那大約是15到64歲人口的2%。在經歷過繭居的人當中,女性佔近一半。有些是跟家人甚至跟配偶同住,可是仍然與社會隔離。
在一項更鎖定目標族群的調查,東京的江戶川區(人口69萬500人)發現該區15歲(含)以上的繭居人口約8,000人。其中三分之一是40-50歲 —— 這個年齡層構成日本媒體命名為「80-50問題」 —— 指80幾歲的父母與50幾歲、有繭居情形的子女同住並撫養他們。
這些中年繭居族有多人是從20幾歲起便蟄居在家,他們的父母往生後他們會變得怎樣是一個引起焦慮討論的主題。名古屋大學心理疾病及心理治療系副教授古橋孝明(音譯)指出,精神科醫師在1970年代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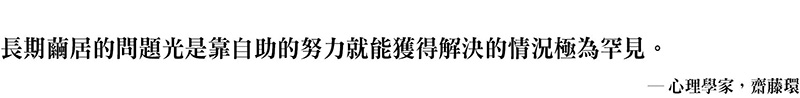
 述一個類似現象為「無感症」,他說:「繭居在2000年左右都只是年輕人的問題。今天,在日本,繭居的延長及年齡的老化已經成為一個極度嚴重的問題。」
述一個類似現象為「無感症」,他說:「繭居在2000年左右都只是年輕人的問題。今天,在日本,繭居的延長及年齡的老化已經成為一個極度嚴重的問題。」在日本苦苦應付福利支出高漲、勞力短缺、繭居族家人心力交瘁之際,有越來越多人想瞭解為何有150萬名日本人活在孤立的狀態中。然而研究人員沒有找到多少答案。即使繭居的行為也已在其他國家發現 —— 最近《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一篇關於美國發現這種情況的文章宣稱「新冠疫情有為美國帶來新一波繭居浪潮之虞」 —— 但對它的根本原因依然缺乏瞭解。《精神病學前線》(Frontiers in Psychiatry)的一份分析將繭居描述為一種「現象」,而非一種特定的精神疾病,雖然潛藏的精神疾病被認為是常見的成因。接受醫療專業人員檢查過的繭居族中,約有一半被診斷出患有精神疾病,例如焦慮、性格或情緒疾患,以及知覺失調或自閉等發展疾病。
古橋已經探討過網際網路及遊戲成癮與繭居行為的關係,他說雖然這兩者並非社交退縮的原因,卻可能是增強因素。古橋說:「好幾個研究顯示繭居與網路或遊戲成癮有關連性。在我的臨床經驗,我可以說沉浸於網路及遊戲的人很難改變社交退縮。」
也有一些跡象顯示日本的社會因素可能也是部分原因。齋藤觀察到在年輕人持續與父母同住比例相對高的國家,社交退縮的傾向也比較強。他也指出除了相信繭居是家庭 —— 而非社會 ―― 要處理的問題之外,難為情或羞恥的感覺可能讓日本家庭不願向外求助。
讓事情更複雜的是,接受內閣府問卷調查的繭居族當中有多達三分之一說他們不想要政府有任何作為來協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有些人可能想要他人協助,可是不是非常確定取得方式,或是他們需要其他仍然涉入他們生活的人推一把才會走出第一步。
對關西大學學生吉村來說,那個推力來自他的家人。在開學後幾個月之內,他的社交退縮開始造成傷害。因為他的靜態生活方式,他增重20磅,他的缺課讓他畢業的可能性十分渺茫。當他隔一年夏天終於
 去看他的家人時,他的父母建議他離開學校,試試不同的事:在鄰近岡山縣的繭居族之家。在花了一些時間取得駕照之後,吉村決定要試試這個團體收容機構。因此,在2017年,在不太確定他會離開多久,或是抵達那裡後會遭遇些什麼事的情況下,吉田收拾行囊,往山裡去。
去看他的家人時,他的父母建議他離開學校,試試不同的事:在鄰近岡山縣的繭居族之家。在花了一些時間取得駕照之後,吉村決定要試試這個團體收容機構。因此,在2017年,在不太確定他會離開多久,或是抵達那裡後會遭遇些什麼事的情況下,吉田收拾行囊,往山裡去。他抵達人類振興營地(Hito Refresh Camp),一個以協助繭居族為目標的相對新的治療觀念。這裡部分算是「支持」場所,部分是集體農場。這裡的日文名字叫人おこし(Hito Okoshi),字面上的意思是「人類振興」,就類似町おこし(machiokoshi)「地域振興」—— 一個經常用在振興日本偏遠社區行動的詞語。這個營地坐落於岡山縣鄉村區域的深山裡,沿著快速道路的引道下來的一條蜿蜒道路前進,再經過不規則延伸的田地及屋頂鋪著光亮黑瓦的老舊農舍。人類振興營地的位置離任何主要城市開車或搭火車都要超過90分鐘,在這個以傑出交通基礎建設互相連結的國家裡,更添一種不尋常的偏遠感覺。
在我造訪的時候,大約有17名繭居族住在該設施,每個人每個月繳交約12萬8,000日幣(約2萬7,300元台幣),重新開始。四周是翠綠稻田及綠樹滿布的山坡,這裡是一個平靜的地方,鼓勵探索內在、人力勞動、以及 —— 非常緩慢地—— 人際互動。
踏進兩層樓的男生宿舍,他們帶我看餐廳、廚房,及一些活動場地。房間很小但很乾淨,每間都有一個單人床、一張書桌,以及收納空間。在廚房,幾位住民一起準備義大利麵當午餐。他們禮貌回答我的問題,可是並不積極聊天。其他住民待在他們的房間,房門關著。這裡安靜得像圖書館。
每位住民—— 即使是一起煮飯的那幾位 —— 似乎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可是假裝自己孤立活在人類振興營地是不被允許的。最起碼住民必須共同維持營地的運作,包括輪流煮飯及打掃。除此之外,當他們
 準備好,他們可以參與集體農場的工作,例如割草。這些活動都涉及與員工、顧問,及傳授技能的當地人互動。住民可以加入每個月舉辦的派對或一起外出,例如去唱卡拉OK、看櫻花,或是鳥取縣知名的沙丘。
準備好,他們可以參與集體農場的工作,例如割草。這些活動都涉及與員工、顧問,及傳授技能的當地人互動。住民可以加入每個月舉辦的派對或一起外出,例如去唱卡拉OK、看櫻花,或是鳥取縣知名的沙丘。吉村剛到這裡時,只做規定他必須做的事,僅止於此。可是,最後,他開始承接更多責任。他開始割草,然後他在當地一個照護企業兼職。他的轉捩點是在他看著別人在廚房準備餐點的時候。吉村說:「有一位前經理對於製作咖哩粉非常講究,成果很棒,我心想:『哇,我也想這麼做。』因此我開始研究我喜歡的菜餚的食譜,像是嫩煎醃番茄醬及韓式辣醬雞肉。我瞭解到為他人煮飯及打工時,你會培養出責任感,意識到其他人依賴你—— 這是我在大學時感受不到的。」
對他人的責任感,日復一日地落實這種責任感,到了最後給予吉村他踏出繭居狀態所需要的自信心。在住了6個月後,他在房間裡收拾他抵達時帶來的行李。他搬出人類振興營地,在附近租了一間公寓。他找到照護的全職工作,白天照顧年長者,從替他們洗澡到協助他們取得政府服務各種事務都做——一個需要每天、親密人際互動的工作。
擔任這個工作5年的吉村正努力要成為一位照護經理,這是協助確保年長者的需求都有獲得滿足的專業社工人員。在放假的時候,他補眠,上健身房,在運動中心打桌球。他仍然認為他自己是獨行俠,說他沒有可以稱之為朋友的人,可是他再也很少打電動了,並經常與他人互動。他的人生—— 一度是活在牆壁後面 —— 現在已經是活在這個大千世界裡。
吉村在人類振興營地待了6個月,可是住民平均停留的時間是11個月,該營地居住最久的記錄是4年。有些人只住了一個月就覺得那裡不適合他們。在我拜訪期間的17位住民當中,只有2個人除了打掃及煮飯的工作外,全時間待在自己的房間。
根據經營這個共享設施的非營利組織「山村企業」(Sanson Enterprise)的代表理事能登弘次(音譯),大約有一半的住民有憂鬱等心理疾病或是自閉症光譜疾患等發展問題。當住民準備好繼續向前走,能登與其他工作人員會幫助他們獨立生活,提供支持計畫協助找到工作及居住的地方。
原來是高中老師後來是平面設計師的能登,在2011年強震及海嘯襲擊他家鄉仙台附近後搬到岡山。他對鄉村振興產生興趣,發起一項計畫來吸引中輟生及失業青年——有時候統稱為「尼特族」(為「非就業、受教育、受訓狀態」的英文縮寫NEET的音譯)——來到人口流失的鄉村,他們可以住在許多閒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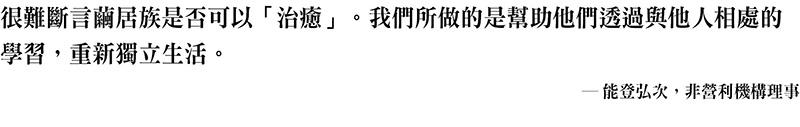 房子裡。他在2016年與人共同創立山村,在一棟原先是鄰近高爾夫球場員工宿舍的建築,創辦了人類振興營地。
房子裡。他在2016年與人共同創立山村,在一棟原先是鄰近高爾夫球場員工宿舍的建築,創辦了人類振興營地。像人類振興營地這樣的設施並不只是唯一的治療方式。有些繭居族嘗試個人及團體治療,或是結合兩種。在《精神病學前線》最近刊登的一篇論文中,古橋描述一個案例研究,提到兩名日本繭居的大學生花了3年參加跑步、騎自行車等戶外活動及羽毛球等運動—— 這些活動不具威脅性,因為其社交互動是有限的。研究人員觀察到,這些活動讓這兩個學生在不會引發社交恐懼的狀態下互動,在介入結束的時候,「兩個人都恢復到正常生活的狀態」。一名學生回去學校上課,另一名找到新工作。
能登說人類振興營地的基本政策,是建立在其理事以及專攻相關身心問題之醫師的經驗及建議。相較於其他繭居族的團體住所,這裡的規則相當鬆散。他看過許多繭居族來來去去,談到有些人克服了隱蔽的
 傾向,後來還談了戀愛。一位18歲的男子在與大阪的父母決裂後搬到人類振興營地。他反社會,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間,對他人使用辱罵的言語,拒絕參加煮飯及家事分工。
傾向,後來還談了戀愛。一位18歲的男子在與大阪的父母決裂後搬到人類振興營地。他反社會,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間,對他人使用辱罵的言語,拒絕參加煮飯及家事分工。如果您或您認識的人正在經歷心理健康方面的緊急情況,請致電或發送簡訊(988)或至988lifel ine.org與988美國的自殺和危機生命線(988Suicide & Crisis Life line)聯繫。如果您在美國以外的地區,請至findahelpline.com,聯繫您所在國家的服務。
儘管如此,在住在宿舍幾年後,他開始與另一位住民交往。最後,他們一起搬到一間公寓。這段關係沒有長久,這名男子最後買了一輛車,以車為家一陣子。他到處打零工,賺餐費及瓦斯費,可是無法穩定持續做一分工作。
最近,這位現年23歲的前住民,騎著他父親買給他的摩托車來到人類振興營地。他宣布他在大阪鐵路機廠找到一個開堆高機的全職工作。這是個理想的工作:他是個鐵道宅,薪水也不錯。除此之外,他與父母修補好關係,也找到新女朋友,正在存錢以便同居。跟5年前的暴躁青少年相比,他已經脫胎換骨。
能登說:「他本來有很多問題,可是漸漸地,他改變他的人生。很難說繭居族能否被『治癒』。我們所做的事情是藉由與他人共同生活,幫助他們再度獨立生活。他們內心很寂寞,有一種沒有人在意他們的感覺。我們想要用歸屬感來取代這些感覺,不只是住在這裡的期間,還有在他們離開之後。」
這篇文章原來是刊登在《開心的理由》(Reasons to be Cheerful),作為「康復」系列的一部分,由惠康信託基金會(Wellcome Trust)所贊助。詳情請參見reasonstobecheerful.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