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即將滿週年之際,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主編Wen Huang
前往歐洲,親眼見證扶輪社員
如何回應這場人道危機。
在分為兩期的報導中,
Wen Huang在第一期描述
他如何取道波蘭前往烏克蘭。
攝影:Ed Zirkle
星期二,7時45分,華沙
當我走出華沙中央火車站時,映入眼簾的是硬石餐廳(Hard Rock Cafe)閃亮亮、吉他造型的招牌。我拍張照片,傳給一位記者朋友,他太太以前曾在收集前共產國家的硬石餐廳T恤。她及其他流行文化的專家相信,東歐的共產主義垮台與搖滾樂有很大的關係。以我的觀點來看,這個招牌大喇喇宣告著波蘭的現代樣貌。
當我轉頭欣賞華沙市中心的其他風景時,我看到文化科學宮(Palace of Culture and Science),拔地而起近800英尺的龐然大物目前仍是波蘭第二高的建築。這棟類似紐約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的蘇聯式高樓於1952年動工,在史達林死後完工,乃是莫斯科送給不聽話的衛星國家的禮物。夜晚時波蘭人用黃色及藍色―― 烏克蘭國旗的顏色——來照亮這棟建築,表示與受圍攻的鄰國團結一心。這個波蘭共產統治歷史的象徵,俯瞰著附近裝飾著聖誕節燈飾及展示西方流行品牌之霓虹招牌的數家購物中心。
時間接近晚上8點,雖然我在察看火車站外的周圍環境,思緒還是圍繞在未來幾天的行程。在我的記者生涯中,我報導過世界各地的國際危機、武裝革命及天災。因此我想要到烏克蘭親眼看看自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後便受苦忍耐之數百萬烏克蘭人的現況。
 從我在芝加哥的住家,我密切留意這場戰爭的新聞。為扶輪工作的我幾乎每天都會聽到社員協助烏克蘭人―― 包括被迫逃往鄰近國家者―― 的報導。在我擔任總編輯的《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我們早期每週與烏克蘭的扶輪社員開視訊會議,在入侵的最初3個月,我們看到扶輪基金會募集150萬美元來支持那些幫助受戰爭波及者的提案。這一切都讓我更想親自體驗火速援助烏克蘭之人道大軍的團隊精神。
從我在芝加哥的住家,我密切留意這場戰爭的新聞。為扶輪工作的我幾乎每天都會聽到社員協助烏克蘭人―― 包括被迫逃往鄰近國家者―― 的報導。在我擔任總編輯的《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我們早期每週與烏克蘭的扶輪社員開視訊會議,在入侵的最初3個月,我們看到扶輪基金會募集150萬美元來支持那些幫助受戰爭波及者的提案。這一切都讓我更想親自體驗火速援助烏克蘭之人道大軍的團隊精神。然後,去年秋天在我到柏林度假時,一個意外的機會來到。烏克蘭的扶輪區域雜誌《Rotariets》的發行人斯特布爾揚科(Mykola Stebljanko)邀請我到烏克蘭西部最大城市利沃夫(Lviv)。因為利沃夫靠近波蘭邊境,他建議我與他及其他扶輪社員一起參加當地一場基金會的研討會。我必須做的就是前往華沙,一切從那裡便會順利開展。
這便是我為何於10月的這個夜晚在波蘭首都徘徊,站在硬石餐廳招牌下等著寶琳娜‧寇諾普卡(Paulina Konopka)―― 華沙市(Warszawa City)扶青社創社社長。寶拉―― 這位30歲的扶青社員喜歡大家這麼叫她――帶我到附近的餐廳,一邊吃著義大利香腸比薩,一邊告訴我戰爭開打時,她與家人正在飛往馬爾地夫的班機上。在飛機降落後,她便立刻聯繫華沙的扶青社友,一起腦力激盪可以協助的方法。她說:「在第一個月,我們整個國家,從政府到民間企業,都似乎停頓下來協助波蘭境內的難民及烏克蘭人民。身為扶輪的一分子,你的直覺就是伸出援手。」
利用社群媒體,華沙的扶青社員向其他國家的友人募款。寶拉的扶青社與威蘭諾國際(Wilanów International)扶青社合作,在郊區為約40名烏克蘭女性及兒童設立一個長期住所,並為難民辦理社交活動,從烹飪到迪斯可派對都有。扶青社員在週六拜訪他們,帶來禮物卡並開車載他們到商店。寶拉說:「我們每個星期也去教他們波蘭語及英語,協助他們適應新國家的生活。」
在戰爭開打後一個月,波蘭已經收容近200萬名烏克蘭難民;約有30萬人住在華沙,可是許多人後來都回去祖國,包括扶輪收容所40位住民的近半數在內。
 寶拉解釋說:「許多人只是想念祖國、夫婿、兄弟,及祖父母。」波蘭政府給予的食品及交通補助終止,以及戰爭導致的能源及糧食漲價也可能都是因素之一。寶拉說她及扶青社友將繼續幫助那些留下來的人找工作及學習波蘭語。
寶拉解釋說:「許多人只是想念祖國、夫婿、兄弟,及祖父母。」波蘭政府給予的食品及交通補助終止,以及戰爭導致的能源及糧食漲價也可能都是因素之一。寶拉說她及扶青社友將繼續幫助那些留下來的人找工作及學習波蘭語。秋天時,當俄羅斯加強對烏克蘭城市的轟炸,寶拉說人們可能再度被迫逃到波蘭,華沙的扶青社員將「準備好歡迎並協助他們」。
回到飯店的酒吧,我看到艾德‧瑟寇(Ed Zirkle),他是俄亥俄州的扶輪社員,是一位攝影師兼紀錄片導演。他邊啜飲著加冰塊的伏特加一邊說:「當我在電視上看到烏克蘭所發生的不公不義,我覺得自己必須到那裡記錄這些事。」因此,當他得知利沃夫扶輪社將主辦一場基金會研討會時,他決定前往烏克蘭,希望能夠與扶輪社員碰面,讓他們帶他到烏克蘭各地。他的請求被轉交給斯特布爾揚科,後者建議我們同行。此時,我和艾德都在等待進一步的指示。
星期三,10時15分,康斯坦欽-耶焦爾納
隔天早上,華沙-蕭邦(Warszawa Fryderyk Chopin)扶輪社前社長傑克‧馬雷薩(Jacek Malesa)邀請我們參觀由位於華沙南部的歷史小鎮康斯坦欽-耶焦爾納(Konstancin-Jeziorna)的扶輪社所設立的難民中心。58歲的馬雷薩在媒體公司擔任稽核,特別請假來陪同我們。他說,為扶輪當義工很有意思。烏克蘭支持及教育中心(Ukrainian Support and Education Center)位於小鎮中心附近,一條安靜街道上一棟3層樓高的水泥建築裡。它的牆壁最近裝飾著美國新罕布夏州學生所製作的藍黃色紙蝴蝶。我們參觀一間擺設簡單的房間,裡頭有二個女孩及四個男孩圍著大桌子坐,在一張切割成手掌形狀的黃紙上畫眼睛和鼻子。起初略帶膽怯的他們很快跟我們熱絡起來,開心聊天。在翻譯努力趕上他們的對話之際,我只能掌握到他們聊天的片段。
這些孩子來自烏克蘭的基輔、赫爾松(Kherson),及卡爾基夫(Kharkiv)。馬雷薩說:「他們的父親在軍中服役,他們和母親及手足來到這裡。與他們親愛的家人分隔兩地讓他們很難受。你應該看看他們剛來的模樣。當時他們對關懷都沒反應,也不太與人溝通。我們提供的照顧大大改善他們的情況。」
在畫畫課結束時,老師帶著孩子出去休息一下。在附近公園的一個小型網球場裡,一個穿著藍色外套、戴著一頂印著“IoDad”帽子的男孩走到角落,把玩著一顆足球。他的眼睛流露著哀傷。穿著紅毛衣的女性走向男孩,給他大大擁抱。這位女性,36歲的露麗雅‧車卡比納(Luliia Cherkasbyna),乃是男孩的輔導員。她來自基輔,戰後便一直在華沙。在家鄉,她輔導有社會化問題的自閉症青少年。她說:「我喜歡在扶輪中心工作,因為我覺得我是在為我的祖國做事。」
去年6月,在該中心開辦之前,扶輪社員邀請以色列的一流心理治療師來訓練烏克蘭心理學家治療及輔導兒童。她指著孩子們的方向說:「你看,他們在微笑。看到扶輪及波蘭的善心人士讓這些孩子所產生的改變,便覺得一切都值得。」
星期三,下午3時30分,華沙
馬雷薩帶我們到位於樹林裡的一間傳統波蘭餐廳。在我們喝著羅宋湯,等著我們點的韃靼牛肉、波蘭餃子,及鬆餅之際,馬雷薩把他的手機拿給我。華沙-蕭邦扶輪社社長麥可‧史庫普(Michał Skup)打電話來,告知我們旅遊計畫的最新進展:我和瑟寇將前往波蘭的札莫希奇鎮(Zamość),烏克蘭的扶輪社員會在當地與我們會合,陪同我們幾天,一起穿越邊境到利沃夫。

因為史庫普的扶輪社是依我最喜愛的作曲家命名,我建議在我們前往札莫希奇之前,先到華沙中心的皇家浴場(Łazienki)公園,在蕭邦雕像前拍個照。
穿著深藍色運動夾克及白襯衫、戴著眼鏡的史庫普看起來體格十分好。在一家跨國企業的波蘭分公司擔任法律總顧問的他最近剛完成從華沙到義大利托斯卡尼、為期10天的自行車之旅,全長約1千英里,目的是募款為難民中心添購一輛小型廂形車。在我描述到該中心參觀的情形後,史庫普便用英語——他的青少年時期大半在美國度過——分享關於該中心創立的一些幕後故事。
他回憶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波蘭人大為震驚,許多人加滿油箱,擔心如果俄羅斯鎖定波蘭為目標可能必須逃走。他說:「我太太打包我們的東西,準備俄羅斯人來了就要走。所幸,世界各地這麼多好人的善心消除我們的恐懼。他們透過我們設的網站聯繫我們,問我們他們要如何幫忙。」
史庫普等人成立一個工作團隊,最高峰時包括世界各地14個扶輪社或地區的代表。他們每週開視訊會議,討論募款及提供救援的方式。史庫普說:「起初我們不知道戰爭會持續多久。許多難民都處於待命模式,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他們需要支持來建立韌性及過正常的生活。我相信這場戰爭不會很快結束,因此我們必須思考如何用永續的方法來協助
難民。」
去年9月,在扶輪基金會災害救援基金及當地企業、個人與德國、加拿大、日本、韓國與美國之扶輪社員捐款的協助之下,該團隊開設這個中心。它聘僱並訓練心理學家、教師,及一位中心經理―― 幾乎所有人都是烏克蘭難民―― 來提供諮商及教育給因戰爭心靈受創的兒童及其他人。史庫普說:「對我來說,這整件事似乎不像是真的。即使我們在烏克蘭體驗過這麼多邪惡的事,扶輪這些善心人士自動自發來到我們身邊,提供協助。這樣的善良實在難以置信。」

在對話期間,史庫普不只一次提到亞力克斯‧雷伊(Alex Ray)的名字。雷依是美國新罕布夏州樸利茅斯(Plymouth)扶輪社員,提供超過30萬美元給該中心。史庫普說:「他現在人在烏克蘭。或許你會遇到他。」

 史庫普呼應寶拉在前一個晚上告訴我的話— 如果俄羅斯升高戰事,可能會有更多人到波蘭避難。有鑑於此,再加上雷伊捐款之助,史庫普及他在扶輪的同事希望長期投入擴展該中心的業務,來提供日間照顧、職業及語言訓練、心理協助,及基本醫療服務,給來自其他國家的難民,包括俄羅斯及白俄羅斯。史庫普說:「我們是個相對小型的扶輪社,只有17名社員。可是我們幫助他人的清楚承諾驅動社員成長,我們預計很快會增加至少3名新社員。」
史庫普呼應寶拉在前一個晚上告訴我的話— 如果俄羅斯升高戰事,可能會有更多人到波蘭避難。有鑑於此,再加上雷伊捐款之助,史庫普及他在扶輪的同事希望長期投入擴展該中心的業務,來提供日間照顧、職業及語言訓練、心理協助,及基本醫療服務,給來自其他國家的難民,包括俄羅斯及白俄羅斯。史庫普說:「我們是個相對小型的扶輪社,只有17名社員。可是我們幫助他人的清楚承諾驅動社員成長,我們預計很快會增加至少3名新社員。」說到這裡,史庫普在蕭邦雕像前擺好姿勢,伸開雙臂,展開他們社的社旗。在照相後,我端詳這座於1926年樹立的雕像在1940年遭德軍破壞,於1958年重建。就在那時候我注意到雕像底座的刻文:「火焰將焚毀我們美麗的歷史,揮劍的盜賊將掠奪我們的珍寶,樂聲將會獲得拯救。」
這段文字來自某些人心目中最偉大的波蘭詩人亞當‧米基威茲(Adam Mickiewicz),可是這些話同樣適用於描寫烏克蘭。
星期二,下午5時15分,札莫希奇
華沙到札莫希奇搭巴士要4小時,穿越波蘭的鄉間地區。當我和瑟寇在傍晚走下巴士時,Google地圖顯示我們離烏克蘭邊境不到40英里。黑夜很快籠罩四周,10月的空氣帶著木頭燃燒的刺鼻味。隨著能源價格飆漲,這裡及歐洲各地許多人家以柴火及燒柴的爐子來溫暖住家。
札莫希奇建立在連接西歐、北歐與黑海的中古貿易路線上。這座由義大利建築師莫蘭多(Bernardo Morando)所設計的城市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儘管居民頑強抵抗,甚至許多人犧牲性命,還是被納粹佔領。當時納粹有系統圍捕猶太人,將他們遣送至集中營。我懷疑這段臣服的悲傷歷史造成小鎮居民在這次危機中展現驚人的同理心。在去年3月的新聞報導中,官員說約4,000名難民已經在城市中找到避難所。
我們住的莫蘭多(Morando)飯店位於妥善修復、迷人的大市集廣場(Great Market Square)邊緣,廣場形似義大利比薩。在這個完美廣場的周圍,多色彩的文藝復興建築並肩而立,屋頂線條模仿16世紀的建築。我和瑟寇拖著行李走進富麗堂皇的接待大廳時,巧遇亞力克斯‧雷伊,就如同史庫普所預測的一樣。在友人協助下,雷伊已經募集130萬美元,所有都將用來資助烏克蘭的人道計畫—— 然後再以近乎1比1的比例,從自己的口袋捐出100萬美元。
身為新罕布夏州廣受歡迎的「普通人」(Common Man)餐廳集團老闆,態度溫和無傲氣的雷伊與40年老友、同是扶輪社員的史提夫‧蘭德(Steve Rand)以及他們的伴侶——麗莎‧穆爾(Lisa Mure)及蘇珊‧馬席森(Susan Mathison)——同行。他們剛從第二趟烏克蘭行回來,目的是要瞭解在烏克蘭人因為停電開始為一個黑暗、寒冷的冬天準備之際,最迫切需要什麼物資。
78歲的五金行老闆蘭德說:「去年3月,當我們看到俄羅斯坦克開進烏克蘭的畫面,感覺充滿壓迫感。這就像是二次世界大戰類型的軍事行動即時上演。所有的戰爭機器都被用來對抗沒什麼能力自保的平民。」
雷伊點頭表示同感。他說:「這是一個單向的侵略,不公平、不正義。我能理解經歷這項悲劇之無辜平民的感受。就好比我們幫助過的美國颶風災民,除了沒人知道我們的協助要如何送抵烏克蘭。」
因為雷伊與蘭德是新罕布夏州樸利茅斯扶輪社員,他們透過該組織找到解答。雷伊說:「我們決定運用我們在波蘭及烏克蘭的扶輪網絡,將其當作管道。這麼一來,我們可以向捐款人保證他們的錢會直接用在烏克蘭的人民
身上。」
雷伊與他慷慨的朋友決定在家鄉的州募款。他們的努力贏得當地政治人物、廣播電台、小聯盟棒球隊,及當地非營利組織的支持,後者包括擔任這項運動之財務代理機構的「花崗岩聯合勸募」(Granite United Way)。雷伊也讓他的850名餐廳工作人員參與,後者分發卡片及小冊子給顧客。雷伊的伴侶穆爾說:「我們很驕傲人口只有138萬的新罕布夏州能夠捐出約每位居民捐1元的金額。」
雷伊說他們正在擴展到新罕布夏州以外的地方。去年夏天,他和朋友在波蘭及烏克蘭進行一項復興任務,並找出六項計畫―― 包括史庫普及其扶輪社所建立的難民中心以及克拉科夫(Kraków)扶輪社購買來支持烏克蘭醫院的捐血車。他們也透過札莫希奇的扶輪社員採購及分送約700公噸的食物。他說:「我們成功的原因便是這裡的扶輪社。他們知道烏克蘭的局勢,並負起責任運用我們的資金把援助送到需要的地方。」
對我即將進行的烏克蘭之旅略感不安,我詢問這些旅人是否擔心安全問題。因為總是渴望分享故事、被我戲稱為這群人之公關經理的馬席森回答:「5月那次行程是我第一次進入戰區。我只是個普通的、中年、中產階級母親。我從未想過自己會出現在那裡。在我們前往利沃夫之前,接待我們的主人警告說之前一直有轟炸,並詢問我們是否依然想去。我心想:有數百萬名烏克蘭人每天醒來都要面對轟炸,卻有勇氣給小孩吃穿,確保他們安全。如果他們做得到,那這麼做個幾天便是我的職責,並運用這個經驗來給予他們長期的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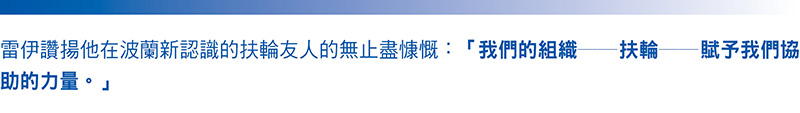
這四個人接著描述他們在烏克蘭的見聞:一個會議中心及蘇聯時代的軍營化身為簡陋的難民收容所,臨時搭建的倉庫協調把食物緊急運送至烏克蘭東部,他們設法協助重建的一間老舊育幼院。雷伊讚揚他在波蘭新認識的扶輪友人的無止盡慷慨:「我們的組織―― 扶輪
―― 賦予我們協助的力量。」
他們的10月行證實了烏克蘭兒童將面臨寒冷冬天的恐懼。雷伊及朋友在12月中回到烏克蘭。在這次的行程中,他裝扮成雪老人(Father Frost,譯註:當地傳說中類似聖誕老人的角色),運送18公噸的食物、1,000個睡袋,及24個發電機——連同1,300個聖誕包裹—— 到利沃夫及羅夫諾(Rivne)的育幼院。
如果他們四人沒被喚去吃晚餐,我們的訪問可能還會再進行個4小時。我朝飯店房間走,當我進門時,我的電話開始響。那是華沙-貝爾威德(Warszawa-Belweder)扶輪社社長皮歐特‧帕多斯基(Piotr Pajdowski)打來的。他叫我要準備就緒:早上會有兩名扶輪社員到飯店陪我和攝影師跨越國界。
早上9時,瓦索‧波隆斯基(Vasyl Polonskyy)及亨納迪‧克羅伊奇(Hennadii Kroichyk)慢慢走進飯店大廳,來自新罕布夏州的四個人及一位來自札莫希奇的扶輪社員正在等著退房。光是提到扶輪便可消除這群陌生人之間的語言或文化隔閡,我們像老朋友般跟彼此打招呼。對話熱絡到我們把行李袋都丟在瓷磚地板上,亂成一堆。
然後,我們出發了。
波隆斯基停下來載我繞了札莫希奇風景美麗的區域兩圈,以求好運,這是我們的下一站——烏克蘭——唯一需要的東西。
下個月:在《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3月號,Wen Huang會描述他到烏克蘭文化之都、遭受圍城的利沃夫的經過來結束他的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