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與我
2025/02/05
閱覽數 375
作者 撰文:Charles D. Allen 插圖:Adrian Brandon
分享至
我一生的座右銘,來自金恩博士、林肯總統及扶輪
 前一晚,我與母親及手足圍坐在電視機前聽到了這個消息。隔天,1968年4月5日,像往常清晨一樣準備送報時,我看到《克里夫蘭簡報》(Cleveland Plain Dealer)的新聞標題,更強化了那殘酷的現實: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在孟菲斯遇刺身亡。他去那裡支持正在罷工的清潔工人,即使在生命的最後幾天,他依然努力使道德宇宙的弧線朝向正義彎曲。
前一晚,我與母親及手足圍坐在電視機前聽到了這個消息。隔天,1968年4月5日,像往常清晨一樣準備送報時,我看到《克里夫蘭簡報》(Cleveland Plain Dealer)的新聞標題,更強化了那殘酷的現實: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在孟菲斯遇刺身亡。他去那裡支持正在罷工的清潔工人,即使在生命的最後幾天,他依然努力使道德宇宙的弧線朝向正義彎曲。金恩博士經常造訪克里夫蘭,長久以來他在我們家一直是個重要的存在。因此,接下來這些故事不僅僅是一段歷史教訓,還與我個人有深刻的關連,因為它們構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在我的腦海中,我清楚地記得在祖母客廳的牆上,有福音歌手瑪哈莉亞‧傑克森(Mahalia Jackson)、甘迺迪總統,及金恩博士的照片圍繞著耶穌基督的畫像。我還清晰地記得1963年8月,我們再一次圍坐在電視機前,觀看華盛頓大遊行。金恩博士站在林肯紀念堂的台階上,發表了那場永垂不朽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講。
我當時只有8歲,但即使在那麼小的年紀,我也仔細聆聽站在台階上的那位所說的話,並思索著他的未來 —— 以及我們的未來。1950年代,我祖母從阿拉巴馬州搬到克里夫蘭,與我的母親及其他家人團聚,而我的父親也與他的手足一同來到這裡。他們是非裔美國人從南方大遷出歷史性行動的一部分。我的父母懷抱著希望,開始在北方成家立業,尋求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在1963年8月的那一天,我們是否已經朝金恩博士所說的那個時刻更邁進一步?那個我們都能夠「一起坐在同胞之愛的餐桌旁」的時刻。
然後,我的世界崩塌了。1966年夏天,我們位於克里夫蘭東區的社區成為縱火、逮捕,及死亡的中心地帶,而這一切的起因是一場突顯出種族主義在北方與南方一樣猖獗的事件。在那場被稱為「霍夫暴動」的6天動盪中,一輛國民警衛隊的車輛停在我們公寓旁的空地上。我越來越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似乎陷入瘋狂的世界裡。
在這樣的動盪時期,我的家人依靠金恩博士尋求精神上的指引和希望。1968年4月的那個早晨,當我看到報紙上的標題 —— 金恩博士被槍殺 —— 我擔憂連希望都拋棄我們了。就在金恩博士遇刺前11個月,我的父親在伊利湖的船難中過世,留下了我的母親及她的5個孩子。我當時12歲,是家中長子,早上送《簡報》及下午送《克里夫蘭新聞報》(The Cleveland Press)是我為家裡分擔的一部分責任。但我對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未來感到茫然。我已經不僅在思索要去哪所大學,還要思考如何負擔學費,還有如果我離開了,我的家人該怎麼辦?我的腦中充滿了疑問,但卻缺乏答案。
在金恩博士遇刺後的那一週,我的初中班級在春假期間前往華盛頓特區。這是我第一次踏出克里夫蘭,接觸外面的世界。我們乘坐巴士旅行,在賓夕凡尼亞州的蓋茲堡戰場停留。當時,美國正過渡到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所謂的「偉大社會」,所以雖然對時事有許多討論及辯論,但對歷史的關注並不多。我對南北戰爭知之甚少,也不記得那次旅行中老師是否對蓋茲堡的歷史提供過任何見解。對於我們這群年輕學生來說,這主要是一次冗長且乏味的巴士旅途中一個令人歡迎的休息站。
在華盛頓,我們參觀了那些常見的景點。我們造訪了白宮庭園、史密森博物館群 —— 以及林肯紀念堂。此時回想,那是我的未來開始成形的時刻。我懷著敬畏之心站在那張巨大的大理石椅旁,丹尼爾‧切斯特‧法蘭奇(Daniel Chester French)雕塑的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端坐其上。我也肅穆地站在台階上,那是將近5年前,金恩博士發表他最著名演講的地方。我閱讀了刻在石頭上、取自林肯第二次就職演說的話語。雖然我不記得當時是哪一句話觸動了我,但我不知怎地在林肯與金恩之間建立了聯繫。這種聯繫延伸到蓋茲堡戰場,以及當時美國社會在我們國家歷史的關鍵時刻所發生的一切。
我將這些想法帶回學校,與老師和同學們分享。後來,我獲得我的高中頒發的第一屆「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獎」。最終,我進入了大學,儘管我選擇的學校連自己都感到意外。當時有一位陸軍預備軍校的聯絡官定期造訪我們的學校,他在尋找有意進入西點軍校的非裔美國學生。老師們請他來找我,但那時正值抗議四起,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事件 —— 國民警衛隊在這所俄亥俄州大學一次反戰抗議中殺害了4名學生 —— 的記憶猶新,所以我並不感興趣。然而,這位聯絡官一次次回來找我,談到一筆全額獎學金教育能為我開啟的機會。最終,他說服了我。
馬丁‧路德‧金恩博士長久以來在我們家一直是個重要的存在,因此在我的故事中不僅僅是一段歷史教訓。
在通往未來的路上,我確實遇到了一些波折 —— 主要是膝蓋受傷導致我入學延遲一年,但在國會議員路易斯‧史托克斯(Louis Stokes)的推薦下,我進入了西點軍校。原本,我只打算在西點待兩年,然後轉學到另一所大學,但有趣的事情發生了:進入西點,我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定位,決定留下來完成全部4年的學業。接著,我展開了30年的軍旅生涯,期間曾被派駐德國、宏都拉斯和韓國等地。我還到喬治亞理工學院讀研究所,並在西點任教3年。2008年,我以上校軍階退役,如今我是賓夕凡尼亞州卡萊爾美國陸軍戰爭學院(U.S. Army War College)的教授。
我在從陸軍退休前便已經開始在這所學院任教,並住在政府提供的宿舍裡。有一天,我的鄰居兼同事 —— 另一位上校 —— 邀請我參加一場扶輪社晨間會議。我跟著去了,也喜歡自己看到的。我結識了來自我們社區的許多優秀人士,包括軍方和民間的成員,我看到他們秉持「超我服務」這一個我也能認同的座右銘所做的善事。那時是2004年,從那時起,我便一直是卡萊爾晨間(Carlisle-Sunrise)扶輪社的社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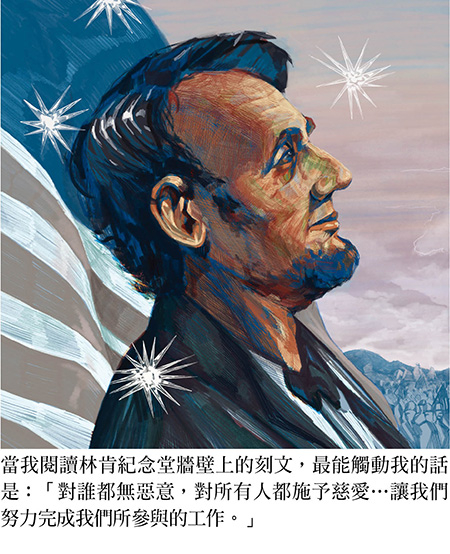 我對扶輪的瞭解越深,越仔細研究金恩博士的著作與演說,就越能看出他的教導與「四大考驗」之間的相似之處。舉例來說,金恩博士於1963年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罕監獄所寫的那封著名信件。當時,他因為非暴力抗議種族隔離而被關押。在信的中間部分,金恩博士強調必須誠實揭示美國的社會不平等:「儘管揭露不公正會帶來緊張,但必須被揭露,唯有在人的良知及全國輿論面前揭露,它才得以解決。」換句話說,他認為我們必須說真話。
我對扶輪的瞭解越深,越仔細研究金恩博士的著作與演說,就越能看出他的教導與「四大考驗」之間的相似之處。舉例來說,金恩博士於1963年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罕監獄所寫的那封著名信件。當時,他因為非暴力抗議種族隔離而被關押。在信的中間部分,金恩博士強調必須誠實揭示美國的社會不平等:「儘管揭露不公正會帶來緊張,但必須被揭露,唯有在人的良知及全國輿論面前揭露,它才得以解決。」換句話說,他認為我們必須說真話。或者在他那篇《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中,他提到美國未能履行其「神聖的義務」,讓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自由及正義,這不正是金恩博士所問,我們的社會是否對所有人都公平?在諾貝爾和平獎的得獎感言中,他強調「學習和諧共處的實用藝術」的重要性時,這不正是對親善與友誼的推崇嗎?而在他名為《鼓號隊隊長本能》的講道中,金恩博士想像在他葬禮可能宣讀的悼詞。他要求悼詞不要聚焦在他的諸多獎項,而只是簡單提到他「努力以生命去服務他人」。無論他有什麼成就,他希望這些成就對所有人都有益。
如今,每當我來到華盛頓,總會想辦法去林肯紀念堂及金恩博士紀念館。站在林肯紀念堂那張偉大的石椅旁,閱讀牆壁上的刻文,最能觸動我的一句話出自林肯的第二次就職演說的神聖段落:「對誰都無惡意,對所有人都施予慈愛…讓我們努力完成我們所參與的工作。」我們在這份工作上取得了一些進展,1964年7月2日,詹森總統簽署了《1964年民權法案》,那一天正是蓋茲堡戰役101週年紀念日的隔天。
而當我來到金恩博士的紀念館時,我會回想起他在林肯紀念堂的台階上所許下的承諾:「我們將從絕望之山中鑿出一塊希望之石。」當我們穿過「絕望之山」 —— 金恩博士紀念館的入口 —— 站在「希望之石」 —— 雷宜鋅雕刻的金恩博士紀念雕像 —— 面前時,我們可以預見這樣的時刻。
2月份,我們慶祝林肯總統及扶輪的生日;它同時也是「黑人歷史月」,這是一個適合回顧金恩博士言論及人生的時刻。這些年來,我聽到過一些聲音說金恩博士可能被過度偶像化。對此我反思過,我認為金恩博士可能會同意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那句話: 「我不是聖人,除非你認為聖人是那種不斷努力的罪人。」
金恩博士勇敢面對並克服了過去的挑戰,為我們贏得今日的幸福。而現在,我們的挑戰是創造一個配得上他夢想的未來。作為扶輪的一員,我們很幸運擁有正確的話語來引導我們前行。

賓夕凡尼亞州卡萊爾晨間扶輪社社員查爾斯‧艾倫(Charles D. Allen)是退休陸軍上校,現任美國陸軍戰爭學院伊萊休‧魯特(Elihu Root)軍事研究講座教授,也是該校指揮、領導與管理系的教授,專攻領導及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