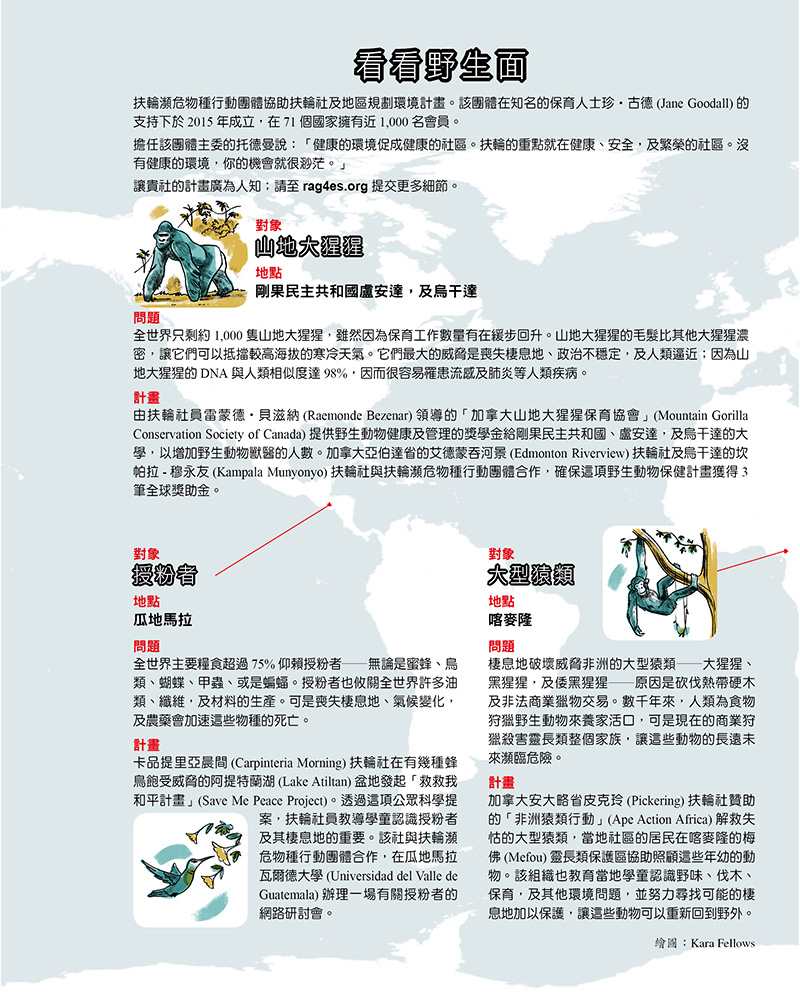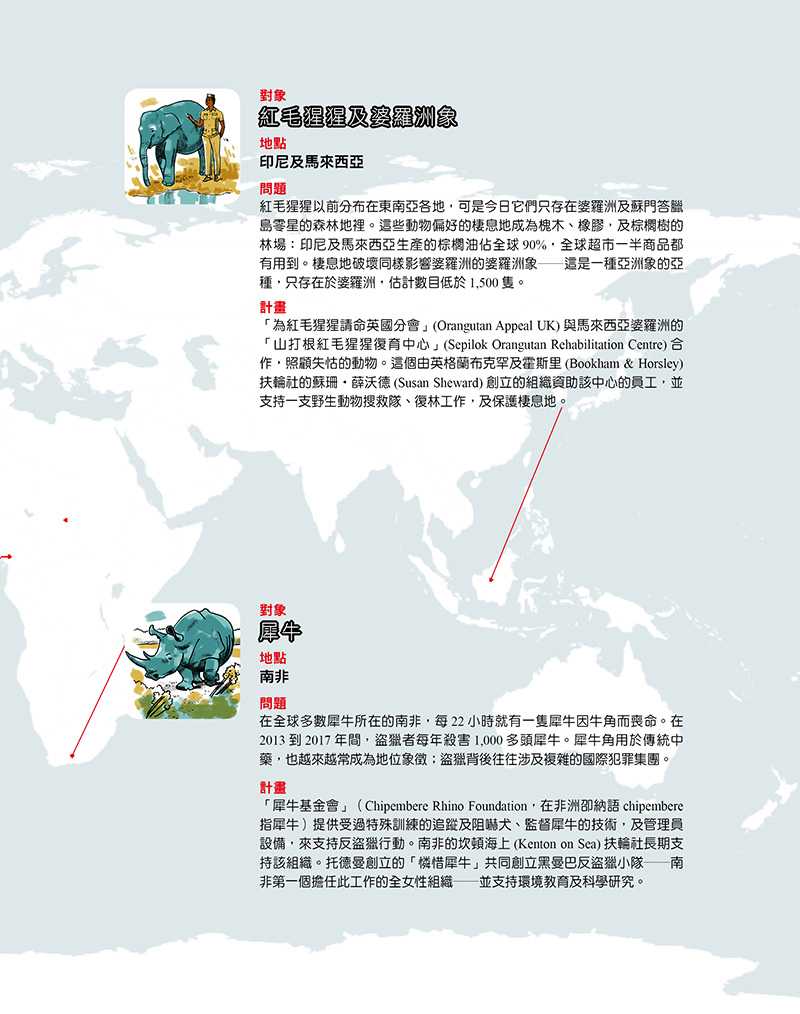茱蒂‧馬拉捷(Judy Malatjie)、馬魯干尼,及祖馬羅在進行巡邏。
全女性的反盜獵團隊可以──
不費一槍一彈── 阻止非洲狩獵
保留區的野生動物犯罪嗎?
穿著寬鬆的綠色迷彩制服及黑色工作靴,長長的馬尾在背上搖晃著,26歲的薩坎妮‧祖馬羅(Tsakane Nxumalo)和她的夥伴,21歲的娜雷迪‧馬魯干尼(Naledi Malungane)沿著一道7英尺高、100英里長的防大象通電圍籬大步巡邏。長著紫色果莢的欖仁樹散發出的強烈、類似蜂蜜的氣味,瀰漫在夏季潮溼的空氣裡,頭頂上有一隻黃嘴犀鳥低空飛略過,停在一棵死亡的風車子木的枝條上。祖馬羅與馬魯干尼是「黑曼巴反盜獵小隊」(Black Mambas Anti-Poaching Unit)的成員。黑曼巴是一種當地土生土長、體長、速度快的劇毒蛇類,該組織努力保護大克魯格國家公園(Greater Kruger National Park)的巴魯勒自然保護區(Balule Nature Reserve)的動物。這座公園位於南非,面積與以色列相當。
祖馬羅與馬魯干尼兩人都在該小隊總部附近長大,可是在加入曼巴小隊後才認識。她們在檢查圍籬有沒有缺口,這是她們21天輪班工作的日常。大多數的時候,還包括收集石塊來補強被疣豬及花豹試圖挖洞穿越的地方,可是偶爾她們會遇到人類剪斷圍籬來獵捕動物的地方。人類狩獵可能是為了野味,但也可能── 更惡劣的──為了獵捕犀牛取牛角。
撰文:Nick Dall
攝影:Bobby Neptune
2013年,第一批曼巴隊員開始巡邏這個保護區,她們很快就發現到盜獵犀牛只是問題的一部分。該公園每年也因為陷阱而有數百隻各種動物喪命。48歲的克雷格‧史班瑟(Craig Spencer)一邊在草原烤肉,一邊聽著鬣狗嚎叫邊回憶說:「真的很丟臉。」他是南非一位特立獨行的保育人士,是私人的巴魯勒動物保護區的守衛隊隊長。「我早該知道在我眼皮底下發生的事。但還是曼巴讓我明白實際的情況。」
黑曼巴這個名字象徵她們有多珍視能夠
進入這個原先是女人止步之行業的機會。
非洲的白犀牛已經遭獵捕到近乎絕種。在非洲剩餘的1萬8,000隻白犀牛中,近90%在南非,也是這種動物的最後希望之地。克魯格的白犀牛又顯然最多,全世界剩餘的5,600隻黑犀牛也有300隻在此處。
犀牛角在某些國家是稀珍品,用於傳統藥材或被看成地位象徵。據野生動物正義委員會(Wildlife Justice Commission)表示,犀牛角在非洲平均可賣到每磅4,000美元,在亞洲每磅更是高達8,000美元。南非的人均所得約每年5,000美元,在新冠疫情前的失業率約29%。因此,說來悲哀,犀牛是很誘人的目標。2017年,盜獵者在大克魯格國家公園殺害500多隻犀牛,包括巴魯勒的17隻。
祖馬羅說:「盜獵者讓我很生氣,因為他們殺害了所有南非人應該好好保護留給未來世代的動物。」雖然祖馬羅完全明白人們盜獵是為了養家活口而鋌而走險,她對這個目標的決心也不會動搖。她指出失去所謂「五大」(Big Five)的任何一隻對觀光業及保育都是一大損失。「五大」是一個古老的狩獵用語,指的是非洲5種最常被搜捕的動物:獅子、花豹、大象、水牛、犀牛。犀牛跟大象一樣,是關鍵的大型草食性動物,可帶給其他物種好處。任何生態系的大型動物通常都像是── 用個老掉牙的說法── 與礦坑的金絲雀一樣,有預警作用。湯姆‧托德曼(Tom Tochterman)說:「如果我們不能防止關鍵物種滅絕,其他物種也就岌岌可危。」
自2009年在南非第一次攝影獵遊「頓悟」
起,現年60歲的托德曼便積極支持這個自然保護區。身為退休的不動產開發商,也是美國華盛頓州契蘭(Chelan)扶輪社社員的托德曼,之後便創立一個名為「憐惜犀牛」(Rhino Mercy)的非營利組織,努力對抗盜獵犀牛,並開發一項奢華攝影獵遊行程,協助籌措保育工作的資金。他也因研究認知失調對消費自然資源的影響及生態系惡化而取得博士學位。
此外,托德曼也是扶輪瀕危物種行動團體的創始會員,該組織的目標是藉由改善各種瀕危動物的棲息地及生活,進而改善人類的生活。他樂見最近國際扶輪增加環境保護這項焦點領域。他說:「我們堅信健康的自然環境有助於健康的社區。」他也補充說:「曼巴證明了反之亦然。」
2010年,托德曼在野營時,與之前擔任過狩獵管理員,現在成為他好友兼夥伴的史班瑟坐在營火前,喝著萊姆酒兌可樂,聊到深夜,談話間他們得到了後來發展為曼巴小隊的靈感。托德曼說:「在非洲各地,對盜獵的預設反應方式一向是引進更多帶著槍的人。這在各地都行不通。」他們突然想到,徹底改變的方式就是塑造下一代的觀念,接觸兒童的最佳方式就是透過他們的母親。
托德曼和史班瑟最後得知有一個政府計畫會聘用女性擔任傳統農業的環境監督者;他們認為可以擴大工作內容來涵蓋「狩獵管理員」,可是南非國家公園的高階主管質疑沒有武器的女性要如何在獅子、花豹、犀牛、大象、及水牛自由行走的區域執行工作。

消息很快傳開,不出幾個月曼巴小隊就幾乎每天都會收到當地女性毛遂自薦。打從一開始,曼巴小隊的日常運作就是由史班瑟的非營利組織「跨界非洲」(Transfrontier Africa)來管理。在興建曼巴的營運基地及女性輪班時休息的獨立營地及籌募資金方面,托德曼都扮演關鍵角色。他也曾在憲兵待過6年,因此他能夠提供套手銬等技巧的訓練。托德曼的「憐惜犀牛」非營利組織擔任曼巴小隊的國際募資單位,為她們取得財務安全。政府最近停止資助這些女性基本工資(大約每個月450美元),這只佔該計畫總支出一小部分而已。托德曼說雇用一支曼巴小隊總計每年費用超過5萬美元。
2014年加入曼巴第二隊的卡蒂柯‧辛姆巴(Nkateko Mzimba)記得她家鄉有許多男性嘲笑她的工作,低估她們在被視為純男性世界的存活率。在她加入曼巴的前幾個月,他們的預測算是相去不遠,她與2名同事不斷遭受某個獅群攻擊,一輛經過的車輛把她們從樹上救下來。她記得說:「我想要辭職,可是在諮商後,我決定留下來,我要證明懷疑者都錯了。」現在是隊長,即將成為專業現場導遊的辛姆巴回顧當時,瞭解到如果她更仔細解讀獅子的行為,就可以避免那種狀況。
辛姆巴現在確保每次巡邏都有一位資深曼巴隊員,也有武裝因應人員隨時待命。(曼巴的每個動作都可從中央營運室來追蹤。)在第一年,曼巴一天找到70個陷阱算是稀鬆平常。她們也在保留區裡面發現好幾處「野味廚房」──大規模屠宰及烘乾肉類的場所。

祖馬羅說,知道曼巴在減少盜獵上發揮功效感覺「真的很棒」,尤其這是一個她一直認為「理應由男性」來擔任的工作。直到今天,南非保育界的許多人仍然覺得女性在反盜獵的世界沒有立足之地,在「五大」區域進行非武裝巡邏是愚蠢行為。祖馬羅笑笑說:「我認為男人不會想要在沒武裝的狀態下到『五大』區域工作。男人會想出很多需要槍枝的理由。可是對我們來說,重點在於解讀動物的行為。我們明白關鍵並不在於槍枝。」
透過她們的社區連結,曼巴也協助改變自南非保育運動開始以來一直造成困擾的警察及強盜的關係。雖然自然保育經常被描述為對抗邪惡盜獵者及掠奪者的保護環境正義使者,卻忽略了更複雜的社會、政治,及經濟現實。1898年就在克魯格國家公園的土地劃分受保護後不久,約有3,000個屬於松加(Tsonga)民族的人被迫從該土地遷離。圍籬架起後,之前只是在地圖上呈現的國界也開始執行,「闖入」這片他們過去居住並獵捕食物的土地還要被罰款或拘禁。在種族隔離期間,圍籬變得更難以突破,判刑也更趨嚴峻。
瞭解管理員及盜獵者可能來自同一個社區── 或家庭── 這段歷史十分重要。這也是一輩子住在這座全世界最具代表性之國家公園邊緣的人為何對它卻幾乎一無所知。
直到今天,南非保育界的許多人仍然覺得
女性在反盜獵的世界沒有立足之地。
祖馬羅以前去過克魯格幾次,可是對野外並沒有特別有親切感。在高分通過團體面試及體能測驗後,她與其他8名成員──包括馬魯干尼──開始接受基礎訓練。她說,訓練很辛苦,包括「只帶著一瓶水整天在太陽底下奔跑」等操練。現在她回顧那段時光卻心存感激:「訓練讓我可以放手去做,我可以成就更多,可以做更多。」
在「五大」區域徒步巡邏數千公里後,祖馬羅愛上原野,對此目標依然投入。她並非特例── 她小隊的所有女性隊員都仍然待在曼巴。她們很自豪傳遞她們所學。祖馬羅說:「我們不僅要教導我們自己的子女;我們還要告訴其他女孩她們什麼都做得到。我們告訴每位女性妳們可以做到更多,妳們可以成就更多。」雖然她們不曾穿著制服回家(盜獵者可能會從曬衣繩上偷走制服,用它來滲透進入公園),祖馬羅並不會掩飾她的工作。她解釋說:「這會激勵他人可以抬頭挺胸走路。我一向都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多。可是曼巴讓我真的發揮內在的潛能。」
曼巴的薪水在當地算相當不錯,因此祖馬羅除了靠這份薪水養活母親與妹妹之外,也支付自己的大學學費。她最近完成教師學位線上課程的第一年。辛姆巴用她的收入來資助及經營一個幫助飢餓鄰居的供餐所──這對減少盜獵也有所幫助。
在曼巴典型的一天包括在日出起床進行圍籬巡邏或掃除陷阱(兩者都是徒步進行)並從遮蔽處或車輛中進行夜間觀察。槍聲、手電筒,及菸味都是盜獵活動的明顯跡象,可是祖馬羅說近日來曼巴比較可能被一隻花豹或一群大象所打斷。她說:「它們在晚上很安靜。有時候它們會擋住去路,可是我們絕對不會催趕它們。」
曼巴每週的工作包括搜查保護區員工及承包商居住的營區、執行道路封鎖、向觀光客及當地社區說明野生動物保育的重要。祖馬羅說:「如果巡邏時都沒事發生,那就是大大成功。如果我沒找到任何陷阱,那更是加分,因為這表示從我前一次檢查到現在都沒人來架設新的陷阱,沒有人切斷圍籬。那令人大大鬆一口氣。」
2015年,精力充沛、笑容具有感染力的魯文‧馬法拉(Lewyn Maefala)加入曼巴計畫,使其獲得一大助力。馬法拉因為就讀許瓦尼科技大學(Tshwa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課程到史班瑟的非營利組織實習一年,此後就再沒有離開。她注意到雖然曼巴巡視圍籬並保護動物不受盜獵者傷害,她們在盜獵者出身的社區所做的預防工作卻不夠。不到幾個月,馬法拉就取得許可到當地4所小學教導環境教育課程。

如果犀牛絕種了,盜獵者就會轉向大象、
穿山甲、獅子骨頭的貿易。保育的重點在
解救所有動物。
到了2017年,馬法拉把這項計畫擴大到10所學校,2個年級,超過1,000名學生。她也利用同樣獲得政府資助的環境監督計畫,聘僱數名年輕男女來教導原野嬰兒。從來閒不下來的馬法拉把這個計畫整合入學校課程(舉例來說,上數學課的學生可以記錄他們在一次獵遊(註:指乘車觀察野生動物)所看到動物的種類、年齡,及性別,並用這份資料來建立一個迷你普查),她也開辦一項種植蔬菜計畫,讓兒童負責觀察整個過程,從翻土到烹煮。她也發起一項「原野奶奶」(Bush Grannies)計畫,運用當地祖母無窮的智慧,與當地一個附屬於南非童子軍的組織合作,確保她的計畫也可以接觸到青少年。去年,超過1,500名青少年參加「原野嬰兒環境教育中心」(Bush Babie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entre)的童子軍會議。史班瑟感激地說:「魯文把原野嬰兒帶領到全新的境界。」
等到祖馬羅於2019年加入曼巴,該計畫已經是全速前進(36位曼巴,包括原野嬰兒小隊),社區對女性管理員的態度也已經軟化許多。她說:「當我回到村莊,其他女性會問我曼巴有沒有缺人。改變心態的感覺很棒,向人們展現女性在對抗盜獵方面也可以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在新冠疫情相關的各種旅遊限制要運送犀牛角跨越國境就更困難、東南亞對犀牛角的需求顯著降低,以及剩餘可獵殺的犀牛數下滑的事實的助力下,證據顯示盜獵犀牛的速度減緩下來。在2021年上半年,盜獵者殺害249頭犀牛── 與2013到2017年相比大幅減少,當時每年有超過1,000頭被捕殺。在曼巴的責任區裡,從2020年初到現在,盜獵者只獵殺了1頭犀牛。
曼巴現在計畫在不久的將來推動一項正式的高中及/或職業訓練計畫,並推廣到南非各地及其他地方,推廣到保護土地及讓更多女性參與的需求都很強烈的地方。讓她們退卻的唯一原因是缺乏資金。托德曼說:「儘管全球疫情為生態旅遊及保育計畫整體帶來衝擊,我們還是會繼續強化我們的計畫。」
馬法拉的「原野嬰兒」激勵第一屆畢業生的2個人去攻讀自然保育相關學位。她會十分樂見該省的每個學校都推行她的計畫,目前也在規劃一輛100個座位的巴士(「想像帶著100個孩子來看克魯格國家公園!」)與附設圖書室以及網路連線的「超級大」的原野嬰兒資源中心。她說:「找到人來推動這個計畫不成問題。我明天就可以找到100個人,可是我們沒有足夠的資金在10所學校推行這個計畫。」
祖馬羅說,這只是必須克服的障礙之一。她說:「我們必須讓曼巴走到公園各個角落。如果犀牛絕種了,盜獵者就會轉向大象、穿山甲、獅子骨頭的貿易。我們需要大象來踩踏樹木,好讓黑斑羚可以吃。獅子需要黑斑羚才能存活。保育的重點在解救所有動物。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如此重要的原因。」
Nick Dall是南非開普敦的一名自由作家。他的新聞報導探索文化與環境的關連性。他出版過兩本有關南非歷史:《罪犯照片》(Rogues' Gallery)及《敗壞的選舉》(Spoilt Ballo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