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麼感覺…
2022/01/26
閱覽數 982
分享至
平凡的扶輪社員們也可能會有非凡的經驗。
由他們親口說出,告訴我們
那是什麼感覺…
繪圖:Richard Mia
贏得牛仔競技錦標賽腰帶扣
傑夫‧克萊恩(Jeff Cline)傑夫‧克萊恩(Jeff Cline)
北卡羅來納州希科里湖(Lake Hickory)扶輪社
 在騎馬方面,我過去只有在度假村騎過幾次是從頭到尾的。但是在2012年,我和妻子去了伯利茲(Belize),這個牧馬人帶我出去騎馬。他說:「你想慢跑嗎?」我說,「什麼是慢跑?」這表示我對騎行知之甚少。當我感覺到馬在我身下漂浮的感覺時,我說:「天哪!這太棒了!」
在騎馬方面,我過去只有在度假村騎過幾次是從頭到尾的。但是在2012年,我和妻子去了伯利茲(Belize),這個牧馬人帶我出去騎馬。他說:「你想慢跑嗎?」我說,「什麼是慢跑?」這表示我對騎行知之甚少。當我感覺到馬在我身下漂浮的感覺時,我說:「天哪!這太棒了!」
當我們回到北卡羅來納州的家時,我租了一匹名叫菸草(Tobacco)的純種馬,之前是賽馬,並開始和他一起訓練。同年,我們去了懷俄明州的科迪(Cody),到那裡看牛仔競技比賽,我第一次看到繞桶賽。你把這三個桶設置相隔30碼左右的距離,你必須以某種模式圍繞它們比賽,而不是把它們撞倒。專業人士疾馳如此之快,並做出這些艱難的轉彎。真令人驚心動魄。就在觀看他們時,我意識到:我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然後我看到一則廣告,上面寫著:「學習如何參加繞桶賽。」這是牧場上的一小時課程。經營這個班的女人戴著這個又大又亮的冠軍腰帶扣。我問她怎麼弄到,她解釋說,要得到一個冠軍腰帶扣,你必須贏得幾場比賽。「嗯,我想要一個,」我告訴她,她說,「你必須去買一個。」她是在開玩笑。但在我的腦海裡,我在想,「好吧,比賽開始!」
我的妻子喬伊(Joy)笑了笑,翻了個白眼。但我們1979 年就結婚了,所以她知道這事會怎麼發展。我開始和菸草一起訓練。我摔過幾次,這是肯定的。我有一次訓練最後被送去急救,縫了8針並做了電腦斷層掃描。喬伊對我那天的騎行很不滿意。那次之後,我答應一定戴頭盔。喬伊給了我一枚有她祝福的一分錢幸運幣,所以我確實有保障措施。
我拼命練習、練習、練習、再練習。雖然我騎馬還不到一年,但無論如何還是開始參加比賽。這些比賽是由國家桶馬協會(NBHA)贊助。當時我57歲,2013年整個夏天我都在參加高級組的比賽。
第二年,NBHA推出了一個新的組別,獎勵一致性而不僅僅是速度。現在,有一些優秀的老牛仔,速度和子彈一樣快。但因為我是最沒有經驗的騎士,所以我想出了一個你可以稱之為數學策略的東西。基本上,我可以騎得很慢,如果我沒撞到桶子,就會積累積分。這有點像那部電影,片中主角意識到他的國家沒有跳台滑雪運動員,所以他學會了跳台滑雪,最後打進奧運。我每週六都去比賽。
到了年底,他們舉行了一場宴會。我不確定我是否贏得了什麼。但我聽到他們叫我的名字,宣布我是北卡羅來納州9區高級5D組冠軍。你可以猜到我得到了什麼。我可能是一隻烏龜,但我的腰帶扣和任何野兔的一樣閃亮。
我現在還在騎馬。一旦你感受到了真正騎馬的感覺,在你心中你就是一名騎士。但我不再參加比賽了。我唯一的目標就是得到那個腰帶扣。我的孩子們去過我騎馬的農場,當然喬伊也看到我參加很多比賽。我記得有一次,我都上馬,準備離開滑道了,然後接到了我未來女婿的電話。他說:「今晚我要向你女兒求婚!」我說:「好吧,孩子。祝你好運。」然後我把手機放回口袋裡,騎得很開心。
到世界各地旅行和服務一年
伊凡‧艾爾巴(Ivan Alba)和 艾琳娜‧盧貞-艾爾巴(Elena Lujan-Alba)
加州拉梅薩日出(La Mesa Sunrise)扶輪社
和他們的女兒,伊莎貝爾(Isabel)及莉莉(Lily)

伊凡:當我們認識然後結婚時,艾琳娜和我都是旅行者。然後我們在2004年生了女兒伊莎貝爾。
艾琳娜:我們和小嬰兒坐在那裡,認為我們不會經常旅行。但當時我們都在小學工作,我們知道六年級那一年孩子們要學習世界文化。所以我們想,與其在書本上研究其他文化,不如帶伊莎貝爾環遊世界。
伊凡:接著在兩年內,我們生了莉莉。[笑]但這只會鞏固我們的決定。
艾琳娜:我們在客廳裡放了一張兒童用的世界地圖。有一回,我們問莉莉她想去哪裡,她說:「我想去剛果!」」我們說,「為什麼是剛果?」她說:「因為那裡有一隻長頸鹿!」果然,在地圖上的非洲中部有一大張長頸鹿的照片。
莉莉:基本上我這輩子都對這次旅行感到興奮。我會在學校向我的朋友吹噓,「我很快就要去環遊世界了!」
艾琳娜:但我們不想這一年只當遊客。我們把女孩們帶到了墨西哥的巴亞爾塔港(Puerto Vallarta),當時她們還小。我們出席了一個扶輪會議,發現該社正在附近做一個服務專案,我們就去幫忙。有一次,我們的孩子們有點無聊。所以我告訴她們去拿他們的著色本和蠟筆。女兒們開始將著色本的一張張撕開並分發蠟筆,突然之間我們有15或20個孩子和他們的媽媽在著色。我們看到我們的女兒們能與別人分享她們熱愛的事物。
伊凡:我們決定,從那時起,我們度假都要含有服務。我們希望我們的女兒們明白,雖然旅行很棒,但如果能在旅途中幫助人,那就更棒。
艾琳娜:一切都剛剛好:我們的家庭旅行變成了一年的扶輪服務。
伊凡:我們存了很多年的錢。我們辭掉了工作、賣掉車子、把房子租出去、把女孩們從學校接出來。我們必須在路上教育他們。加入扶輪陣容使我們不論到任何地方都能與當地社區建立聯繫—— 歐洲、非洲、亞洲、南美洲。扶輪社員們照顧我們,就好像我們是他們自己人一樣。他們會在機場接我們,開車送我們到處看看。透過他們,無論我們走到哪裡,都能與服務專案建立聯繫。
伊莎貝爾:當我們離開聖地牙哥時,我11歲,我記得對於要離家一年感到非常緊張。我必須學會如何靠行李箱生活,一次數天。但在旅行結束時,我注意到我改變多麼大。在我們啟程之前,我對吃什麼以及如何打發時間非常挑剔,但現在我對新事物心態更加開放。這次旅行也激起了我對旅行的興趣。我是一名高三學生,一畢業,我會花一年的時間去旅行。我想做以服務為導向的實習。
莉莉:我想說的是,在那一年裡,我的身心都成長了至少三年。最後我真的很想家。我們最好的經驗之一是在菲律賓,在那裡我們有機會上學。奇怪,我變得懷舊,穿上制服和及膝襪子回到教室。
伊莎貝爾:我喜歡訪問肯亞一個名為「重啟非洲」的專案。這是一個因衝突而被遺棄或成為孤兒的孩子的家,由一位名叫瑪麗‧庫爾森(Mary Coulson)的扶輪社員經營。一百多個孩子,從嬰兒到青少年,住在那裡。
艾琳娜: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托兒所陪一個小女孩,只是聊天和擁抱。這件事讓我產生了這個幻想:要是我們收養她呢?但後來我想:她在那裡過得如此快樂,得到這麼好的照顧,我為什麼要把她從這個地方帶走?
伊凡:這是我們在國外這一年學到的很大一部分:無論你走到世界的哪個地方,你仍然會看到孩子們在笑。你正在訪問一個貧困的地區並不意味著你正在訪問一個令人悲哀的地區。哪裡有充滿愛心的社區,哪裡就有快樂的生活。
莉莉:有一天,我的英語課提到非洲這個話題。有些同學說:「非洲是一個貧窮的地方,我們應該多送一些東西給他們。」我的大腦基本上爆炸了。我設法解釋,非洲不僅僅是一個到處都是值得同情的窮人的地方。
艾琳娜:在我們離開前幾個月,我確實有一陣子在想:哇,我們真的要這樣做嗎?但整個旅程真的是天衣無縫。這太神奇了。我們只有一次在柬埔寨感到驚慌。我們搭乘一輛包租巴士,途中在一個小鎮停下來上洗手間。我讓女孩們先走,當我從洗手間出來時,我看到伊凡站在那裡。巴士不見了。
伊凡:因為艾琳娜在浴室裡待的時間有點長,我不得不做出決定。假如我和女孩們待在巴士上,艾琳娜從浴室出來時,就沒有人在場解釋巴士要回來了。
艾琳娜:是的,你說過了,我說:「下次,不要再單獨留下我的女兒們了。」[笑]我不應該笑。那是我這輩子最長的12分鐘。
莉莉:順便說一句,我不知道巴士要回來了。我嚇壞了。我們姐妹只是坐在那裡聽音樂,彷彿「我們會沒事的。」嗯,我們不會沒事的!我們在柬埔寨,在巴士上,我們的父母不在身邊,也沒有任何方法可與任何人通訊!
艾琳娜:就像我說的,有一點恐慌。但我們確實有一個計畫,如果女孩們不回來的話。我們打算雇一輛計程車去追那輛巴士。
伊凡:在我們整整一年的旅行中,這是所發生最糟糕的事。我們從來沒有遇到扒手或被騷擾。這個世界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可怕。世界到處都是善良和好心的人。不只是扶輪社員而已,我們遇到的每一個人都這樣。這段經歷真的改變了我們對世人的看法。
成為開放水域的游泳選手
麗杜‧凱迪亞(Ritu Kedia)
扶輪青少年交換,印度到美國佛蒙特州,2005-06年度
芭卡‧凱迪亞‧阿格拉沃(Barkha Kedia Agrawal)
扶輪青少年交換,印度到奧勒岡州,1999-2000年度

芭卡:我和我妹妹開始學游泳的地方是我們居住的印度安拉瓦提(Amravati)市運動中心的泳池。可是那時我父親在報紙上看到600公里外的孟買有一場5公里的游泳比賽。他帶我到那裡,讓我下到海裡。當時我9歲。
麗杜:芭卡參加那場比賽的前兩次她沒游完。第三次,她和我姑姑待在孟買約一兩個月,找教練練習。她的教練說:「你知道,對長泳來說,你需要很大的耐力。你必須很堅定。你需要練習。」他認為她具有這些能力。第三次,她成功游完5公里。當時她12歲。
芭卡:我第一次獨泳是在那場比賽之後幾個月。獨泳是這樣子的:那不是和其他選手比賽。你不能碰到船或是上船,否則就失去資格,可是你可以愛游多久就游多久。完成那項泳賽本身就是成就。我的第一次獨泳是36公里。我的下一場是參加瑞士的蘇黎世湖馬拉松泳賽。那是26.4公里的計時賽,選手必須在12小時之內完賽。我獲得銅牌。
麗杜:心理上及精神上,我們家及扶輪大家庭都不斷給我們支持:每次我們游泳比賽完回來,就會有20名扶輪社員帶著花束及花圈及音樂在火車站等我們。他們會邀請我們參加扶輪社例會來分享我們的體驗。
芭卡:我們在童年就接觸扶輪。我們父親基秀‧凱迪亞(Kishor Kedia)曾擔任扶輪社社長,後來還成為3030地區總監。他以前會在我們游泳的泳池舉行他扶輪社的理事會。我父親會和其他理事坐在那裡,我母親會幫我們計算圈數。
蘇黎世湖的比賽後約1年,我參加扶輪青少年交換到奧勒岡州密爾瓦基。我去看波特蘭拓荒者隊的籃球比賽。我參加《森林王子》(The Jungle Book)的戲劇演出。我認為他們給我一個角色的唯一原因是主角毛克利(Mowgli)的女朋友是印度人。
麗杜:我從青少年交換學到的最大收穫就是你心裡想的事就應該去做,否則事後會後悔。佛蒙特州的布蘭登(Brandon)是一個關係非常緊密的社區。學校裡有些人從3歲開始就成為朋友,所以我很難交到朋友。有很多事是我現在認為我當時應該做的,可是我沒有。
隔年,在2007年,我在一個月之內游了4場國際賽。我的第一場開放水域泳賽是直布羅陀海峽,從西班牙游到摩洛哥。之後是希臘的托羅尼歐斯海灣,再來是瑞士的蘇黎世湖,最後是英吉利海峽。當我泳渡英吉利海峽時,我真的已經筋疲力竭了。
芭卡:我認為麗杜可能是開放水域泳賽唯一在一個月之內參加4場國際賽的人。在她橫渡英吉利海峽後,隔天我們到協會辦公室去領證書。他們說,你們是亞洲第一對泳渡英吉利海峽的姐妹。我們不知道有這樣的記錄。我們是全世界第四對。
麗杜:我和姐姐泳渡直布羅陀海峽時,她是女選手第二名。在你下水的地方,場面很混亂,有幾秒鐘你根本不知道誰在撞你。水從四面八方而來。你會覺得你好像在瀑布底下之類的。然後你會想:「好,我們來找一種節奏,開始游泳。」
芭卡:2016年,麗杜到孟加拉,在孟加拉灣國際馬拉松泳賽締造世界記錄。她是參賽的人當中最快的,不分男女選手。可是在比賽期間她還被水母螫傷。
麗杜:我看到一球白白的東西朝我而來。有很長的觸手,感覺就像1,000根針刮過我的手。我大概失去意識幾秒鐘。超級刺痛。就像有人朝你潑強酸。引導我的船上漁夫說:「抓住救生圈,爬上船來。」可是在馬拉松泳賽一旦碰到船就失去資格。所以我說:「只要我還有意識,我就會游下去。」然後我繼續游。非常非常痛。我想我一心只想要把它游完;那就是我最後打破世界記錄的原因。我手和前臂的皮膚花了近兩個半月才恢復正常。
芭卡:在我游英吉利海峽時,天色很黑,正在下雨,風很大。英國的雨很可怕。它像是會割穿你的身體。我父親和教練告訴我要靠近船游來擋風。所以聽到那個巨大聲響時,我保持安全的距離游,可是又很靠近船隻。
麗杜:我至今仍然記得那個聲音。我在船上。大浪打來,船往下。我聽到很大的爆裂聲,我們以為船打到她的頭或是什麼。我仍然記得我父親和教練臉上的表情。他們大聲呼叫她:「芭卡!芭卡!」
芭卡:我以為他們在為我加油,像是:「衝,芭卡!衝,芭卡!」可是後來我瞭解到那個芭卡不是歡呼的口氣,而是擔憂。然後他們看到我還活著,就說:「繼續游!繼續游!」隔天他們才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麗杜:她參加的是那一季的最後一場。那時是9月。那天,她是唯一完賽的獨泳者。天氣糟透了。
芭卡:12點我看到法國海岸時,我所游的距離本該只花45分鐘,可是因為大浪我卻多花了5小時。
麗杜:你聽到很多選手說:「我差一點游泳橫越英吉利海峽。」可是沒有幾乎差一點這回事。你要不是游完,就是沒游完。開放水域是對你身為人的大考驗,因為你是一個人游。你一天練習8小時:上午4小時,晚上4小時,加上每兩星期游一次8到10小時的長泳。
芭卡:如果你想要冒險,挑戰自我,挑戰大自然,那就試試開放水域游泳。對這種游泳來說,你所做的每件事就是代表你這個人。
麗杜:它給你紀律。它給你意志力。它給你信心,因為你覺得:如果我做得到這個,我就做得到人生其他每件事。
步行橫越阿爾卑斯山
亞利山卓‧甘登(Alexandre Gandon)
法國坎城-里維埃拉(Cannes Riviera)扶青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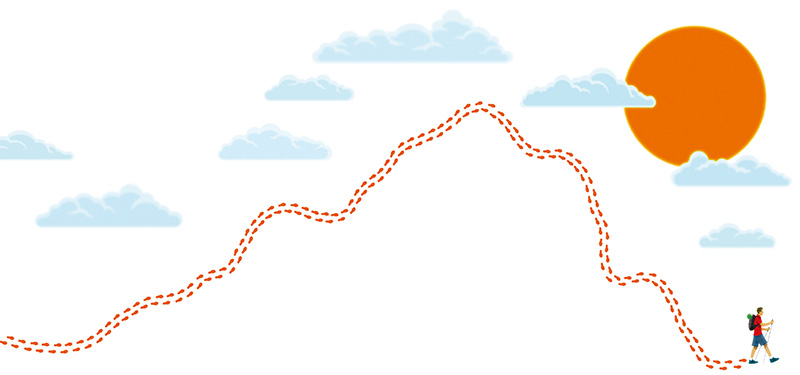
當我開始長距離健行──像是2019年我從法國南部坎城走1,500英里到丹麥哥本哈根── 我的重點從來不是體能挑戰。我只是在我的假期探索另一種旅遊方式。我覺得健行是認識人的最好方法。
2020年夏天,我決定從坎城橫越阿爾卑斯山到日內瓦。路線只有370英里,可是22英里的高度差讓它成為難度很高的任務。為了增加趣味,我計畫在星空下睡覺,所以我只帶一個小背包,空間只容得下兩雙襪子、兩件T恤、一件雨衣、兩條求生毯,以及一個手機用的輕型太陽能充電器。
我也帶一塊特殊香皂每天洗衣服用。在夏天,山區有足夠的太陽及風讓衣服很快就乾,也有足夠的湖泊和河流可以讓我盥洗── 雖然冷水會令人精神為之一振(最保守的說法)。可是健行時保持良好衛生十分重要,而且我看到人或到烘焙坊買麵包時,我想要看起來有把鬍子刮乾淨。此外,我計畫沿路拜訪扶輪社員,例如在法國布聖莫里斯(Bourg-Saint-Maurice)及安納馬斯(Annemasse)迎接我的社員。
當時,我正擔任坎城-里維埃拉扶青社的社長,所以我為這趟健行增添另一個新元素:為某個目標募款。本社其他社員協助募款及媒體宣傳等事務。我們也腦力激盪來挑選一個本地我們可以協助的組織。突然間,我的健行不再是個人而是集體的行動。我們選定「里奧組織」(Association Leo),它資助兒童癌症研究並提供經濟援助及道德支持給罹癌兒童的家庭。它的名稱來源是一個因癌症離世的15歲男孩,創辦人正是他的母親戴芬妮(Delphine)。在我健行期間,她連同她的丈夫及女兒不斷傳送鼓勵的訊息給我,成為很棒的激勵力量。
我在8月1日從坎城的節慶宮會展中心(Palais des Festivals)出發。健行穿越阿爾卑斯山並不如你可能預期的那般困難。當然,我需要做某種程度的體能準備。我做呼吸練習,強化肌肉,在出發前半年,我停止吃肉好讓自己減重,以擁有更適合健行的體態。我之前的健行也讓我準備好面對行程中可能發生的事。我習慣健行,不再會有長水泡的問題。有個有趣的差別,阿爾卑斯山步道的石頭對腳底來說並不如── 比方說── 科西嘉島的硬。後者的石頭更可能碎裂,覆蓋步道的碎石也比較尖銳。
最重要的守則是要喝大量的水,這在阿爾卑斯山區並不困難。即使我不渴,我還是把握每個喝水的機會。我決定只在沿途遇到的商店吃東西,可是我常常可能連續48小時都沒吃。在某些路段有人陪我一起走時我也會得到協助。今年擔任昂蒂布角(Antibes Cap'Azur)扶青社社長的朋友馬修‧梅羅(Mathieu Maero)頭兩天陪我一起走,其他朋友會在沿途與我會合。那時我發現就跟騎自行車一樣,如果有人走在前頭會有助於我向前走。
我沒有固定的路線。我用一個叫做「造訪」(Visorando)的應用程式,上頭可以找到健行步道的詳細地圖。可是我很想要造訪一些地標,包括阿爾卑斯山海拔最高的人工鋪設的隘口── 伊澤爾谷(Col de l'Iseran)。(環法自行車大賽的粉絲對這個地點應該都很熟悉。)我睡在這個隘口最高點附近,海拔近8,000英尺。這是我最具挑戰性的夜晚,溫度降至近華氏44度(約攝氏6.7度)。保暖的一個訣竅就是躺在用松樹樹枝鋪的床上。
絕大多數的時候,我運氣都不錯。我沒想到沿途遇到的阻礙會這麼少。唯一算是意外的一次是有一隻黃蜂叮了我的下嘴唇(我很容易「招蜂」引蝶,經常被叮。)我的嘴唇腫得很可怕,可是我設法找到藥局,嘴唇不到一天就恢復原來的樣子。它讓我學到處理挫敗時不要過度驚慌。
在阿爾卑斯山,你必須當心雷雨;如果遇到了,要遠離樹木,藏好你的步行杖以避免雷擊。健行時,我會注意天候,每次下雨我都會找個有遮蔽的地方補補眠。可是整體來說,老天爺很幫忙,我就如計畫般在8月20日抵達目的地。我們超過我們的募款目標,募得3,000英鎊,相當約3,500美元。為此錦上添花的是日內瓦扶輪社社員為我籌辦的歡迎會,他們辦理一烤肉趴來向我致敬。我必須承認,再次吃肉的感覺很棒。
帶著自體免疫罕見疾病──以及更罕見的狗──活著
米歇爾.穆羅(Michelle Munro)
華盛頓州南惠德貝(South Whidbey Island)扶輪社
 2001年12月10日,我打完籃球後去為聖誕節買東西。回家後,我太太和我開懷大笑因為我看起來就像魯道夫── 我的鼻子和耳朵都是亮紅色的。可是隔天,我就動不了。我無法順暢呼吸。我無法解釋有多痛;我身體的每個部位都在痛。
2001年12月10日,我打完籃球後去為聖誕節買東西。回家後,我太太和我開懷大笑因為我看起來就像魯道夫── 我的鼻子和耳朵都是亮紅色的。可是隔天,我就動不了。我無法順暢呼吸。我無法解釋有多痛;我身體的每個部位都在痛。
我被診斷出患有一種名為復發性多軟骨炎的自體免疫罕見疾病。這個病會讓你的免疫系統攻擊體內的軟骨及結締組織── 你的耳朵、你的鼻子、你的氣管、你的心臟。大多數人都不知道你體內各處有這麼多軟骨組織。當醫生說:「我們會替你轉診給一位風溼病專科醫師,他會幫你治療」時,我心想我可以當天看到醫生。可是其中一位護理師告訴我:「不急。不是說你看了就會改善。」
那不是我想聽到的。我是個非常樂觀的人,所以我開始盡可能多瞭解多軟骨炎這個病,可是當時的資訊比今天少非常多。我在網路上看到的每項資訊都提到診斷後壽命剩3到5年。從那時候起,我就瞭解到那是因為人們太晚獲得診斷。我非常堅信獲得良好的醫療照顧,我會比這個多活很久。
不知道是我吃的某種藥還是這個病本身讓我一眼失明。我不確定我是否另一眼也會失明,所以我開始研究導盲犬。我發現還有其他服務犬,包括適合我這種情況的。填寫申請書和面談的過程真的很困難。我自己之前都在非營利組織工作,提供他人服務,現在我是那個需要幫助的人。
我的第一隻服務犬海頓(Hayden)和我非常親密。我跟他溝通幾乎不用開口。我記得有一次我從樓梯跌到地下室,海頓跑下來查看我的狀況,可是我無法說話,因為我摔斷了幾根肋骨。海頓往樓上衝,我心想:「你在做什麼?」然後他把電話拿來給我,這是他受訓在危急時要做的事。可是我無法打電話,因為我無法說話。所以他再次跑掉。通常在那樣的情況,他會躺下來陪我。可是他跑到我們的後院不斷嚎叫,直到一位鄰居,他有鑰匙,進來房子裡,打電話叫救護車。聽到海頓嚎叫,鄰居知道有事不對勁。
我現在的提歐(Theo)已經養兩年了,所以我們還在瞭解彼此。他會做每件我需要他做的事。當我發作時,即使我太太在場幫我,無論我們在哪,他還是會跑去拿我的疼痛藥來找我。
我盡量保持樂觀,可是新冠疫情不一樣。我打了疫苗,可是因為我的病,我的做法還是像沒打疫苗一樣── 即使戴口罩是個挑戰,因為我的軟骨組織不夠堅固到可以讓耳朵上部不會往前翻起。
我在2020年夏天,疫情燃燒之際加入南惠德貝扶輪社。我很幸運,因為我的扶輪社非常認真看待防疫措施。在Zoom線上例會時,總會有人問:「提歐在哪裡?」提歐佩戴著一條扶輪頭巾,更正式的場合他還會打扶輪領結。他被提名為本社的吉祥物── 即使其他社員也會出現在Zoom畫面的寵物貓狗可能無法完全認同。
由他們親口說出,告訴我們
那是什麼感覺…
繪圖:Richard Mia
 |
|

自從〈那是什麼感覺〉專題在《國際扶輪英文月刊》2016年1月首度推出以來,就是讀者最喜歡的單元之一。現在,從《國際扶輪英文月刊》2月號開始,〈那是什麼感覺〉會成為每個月的固定專題。如果你是扶輪社員且有很棒的故事可說──又或者你認識的某個與扶輪有關的人有很棒的故事可分享── 我們都想要知道。 請把你的故事分享到magazine@rotary.org,郵件主題請包含"What It's Like"的字樣。 請在未來出刊的扶輪雜誌繼續閱讀這些最美好的故事。 |
傑夫‧克萊恩(Jeff Cline)傑夫‧克萊恩(Jeff Cline)
北卡羅來納州希科里湖(Lake Hickory)扶輪社
 在騎馬方面,我過去只有在度假村騎過幾次是從頭到尾的。但是在2012年,我和妻子去了伯利茲(Belize),這個牧馬人帶我出去騎馬。他說:「你想慢跑嗎?」我說,「什麼是慢跑?」這表示我對騎行知之甚少。當我感覺到馬在我身下漂浮的感覺時,我說:「天哪!這太棒了!」
在騎馬方面,我過去只有在度假村騎過幾次是從頭到尾的。但是在2012年,我和妻子去了伯利茲(Belize),這個牧馬人帶我出去騎馬。他說:「你想慢跑嗎?」我說,「什麼是慢跑?」這表示我對騎行知之甚少。當我感覺到馬在我身下漂浮的感覺時,我說:「天哪!這太棒了!」當我們回到北卡羅來納州的家時,我租了一匹名叫菸草(Tobacco)的純種馬,之前是賽馬,並開始和他一起訓練。同年,我們去了懷俄明州的科迪(Cody),到那裡看牛仔競技比賽,我第一次看到繞桶賽。你把這三個桶設置相隔30碼左右的距離,你必須以某種模式圍繞它們比賽,而不是把它們撞倒。專業人士疾馳如此之快,並做出這些艱難的轉彎。真令人驚心動魄。就在觀看他們時,我意識到:我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然後我看到一則廣告,上面寫著:「學習如何參加繞桶賽。」這是牧場上的一小時課程。經營這個班的女人戴著這個又大又亮的冠軍腰帶扣。我問她怎麼弄到,她解釋說,要得到一個冠軍腰帶扣,你必須贏得幾場比賽。「嗯,我想要一個,」我告訴她,她說,「你必須去買一個。」她是在開玩笑。但在我的腦海裡,我在想,「好吧,比賽開始!」
我的妻子喬伊(Joy)笑了笑,翻了個白眼。但我們1979 年就結婚了,所以她知道這事會怎麼發展。我開始和菸草一起訓練。我摔過幾次,這是肯定的。我有一次訓練最後被送去急救,縫了8針並做了電腦斷層掃描。喬伊對我那天的騎行很不滿意。那次之後,我答應一定戴頭盔。喬伊給了我一枚有她祝福的一分錢幸運幣,所以我確實有保障措施。
我拼命練習、練習、練習、再練習。雖然我騎馬還不到一年,但無論如何還是開始參加比賽。這些比賽是由國家桶馬協會(NBHA)贊助。當時我57歲,2013年整個夏天我都在參加高級組的比賽。
第二年,NBHA推出了一個新的組別,獎勵一致性而不僅僅是速度。現在,有一些優秀的老牛仔,速度和子彈一樣快。但因為我是最沒有經驗的騎士,所以我想出了一個你可以稱之為數學策略的東西。基本上,我可以騎得很慢,如果我沒撞到桶子,就會積累積分。這有點像那部電影,片中主角意識到他的國家沒有跳台滑雪運動員,所以他學會了跳台滑雪,最後打進奧運。我每週六都去比賽。
到了年底,他們舉行了一場宴會。我不確定我是否贏得了什麼。但我聽到他們叫我的名字,宣布我是北卡羅來納州9區高級5D組冠軍。你可以猜到我得到了什麼。我可能是一隻烏龜,但我的腰帶扣和任何野兔的一樣閃亮。
我現在還在騎馬。一旦你感受到了真正騎馬的感覺,在你心中你就是一名騎士。但我不再參加比賽了。我唯一的目標就是得到那個腰帶扣。我的孩子們去過我騎馬的農場,當然喬伊也看到我參加很多比賽。我記得有一次,我都上馬,準備離開滑道了,然後接到了我未來女婿的電話。他說:「今晚我要向你女兒求婚!」我說:「好吧,孩子。祝你好運。」然後我把手機放回口袋裡,騎得很開心。
口述由Steve Almond撰寫
到世界各地旅行和服務一年
伊凡‧艾爾巴(Ivan Alba)和 艾琳娜‧盧貞-艾爾巴(Elena Lujan-Alba)
加州拉梅薩日出(La Mesa Sunrise)扶輪社
和他們的女兒,伊莎貝爾(Isabel)及莉莉(Lily)

伊凡:當我們認識然後結婚時,艾琳娜和我都是旅行者。然後我們在2004年生了女兒伊莎貝爾。
艾琳娜:我們和小嬰兒坐在那裡,認為我們不會經常旅行。但當時我們都在小學工作,我們知道六年級那一年孩子們要學習世界文化。所以我們想,與其在書本上研究其他文化,不如帶伊莎貝爾環遊世界。
伊凡:接著在兩年內,我們生了莉莉。[笑]但這只會鞏固我們的決定。
艾琳娜:我們在客廳裡放了一張兒童用的世界地圖。有一回,我們問莉莉她想去哪裡,她說:「我想去剛果!」」我們說,「為什麼是剛果?」她說:「因為那裡有一隻長頸鹿!」果然,在地圖上的非洲中部有一大張長頸鹿的照片。
莉莉:基本上我這輩子都對這次旅行感到興奮。我會在學校向我的朋友吹噓,「我很快就要去環遊世界了!」
艾琳娜:但我們不想這一年只當遊客。我們把女孩們帶到了墨西哥的巴亞爾塔港(Puerto Vallarta),當時她們還小。我們出席了一個扶輪會議,發現該社正在附近做一個服務專案,我們就去幫忙。有一次,我們的孩子們有點無聊。所以我告訴她們去拿他們的著色本和蠟筆。女兒們開始將著色本的一張張撕開並分發蠟筆,突然之間我們有15或20個孩子和他們的媽媽在著色。我們看到我們的女兒們能與別人分享她們熱愛的事物。
伊凡:我們決定,從那時起,我們度假都要含有服務。我們希望我們的女兒們明白,雖然旅行很棒,但如果能在旅途中幫助人,那就更棒。
艾琳娜:一切都剛剛好:我們的家庭旅行變成了一年的扶輪服務。
伊凡:我們存了很多年的錢。我們辭掉了工作、賣掉車子、把房子租出去、把女孩們從學校接出來。我們必須在路上教育他們。加入扶輪陣容使我們不論到任何地方都能與當地社區建立聯繫—— 歐洲、非洲、亞洲、南美洲。扶輪社員們照顧我們,就好像我們是他們自己人一樣。他們會在機場接我們,開車送我們到處看看。透過他們,無論我們走到哪裡,都能與服務專案建立聯繫。
伊莎貝爾:當我們離開聖地牙哥時,我11歲,我記得對於要離家一年感到非常緊張。我必須學會如何靠行李箱生活,一次數天。但在旅行結束時,我注意到我改變多麼大。在我們啟程之前,我對吃什麼以及如何打發時間非常挑剔,但現在我對新事物心態更加開放。這次旅行也激起了我對旅行的興趣。我是一名高三學生,一畢業,我會花一年的時間去旅行。我想做以服務為導向的實習。
莉莉:我想說的是,在那一年裡,我的身心都成長了至少三年。最後我真的很想家。我們最好的經驗之一是在菲律賓,在那裡我們有機會上學。奇怪,我變得懷舊,穿上制服和及膝襪子回到教室。
伊莎貝爾:我喜歡訪問肯亞一個名為「重啟非洲」的專案。這是一個因衝突而被遺棄或成為孤兒的孩子的家,由一位名叫瑪麗‧庫爾森(Mary Coulson)的扶輪社員經營。一百多個孩子,從嬰兒到青少年,住在那裡。
艾琳娜: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托兒所陪一個小女孩,只是聊天和擁抱。這件事讓我產生了這個幻想:要是我們收養她呢?但後來我想:她在那裡過得如此快樂,得到這麼好的照顧,我為什麼要把她從這個地方帶走?
伊凡:這是我們在國外這一年學到的很大一部分:無論你走到世界的哪個地方,你仍然會看到孩子們在笑。你正在訪問一個貧困的地區並不意味著你正在訪問一個令人悲哀的地區。哪裡有充滿愛心的社區,哪裡就有快樂的生活。
莉莉:有一天,我的英語課提到非洲這個話題。有些同學說:「非洲是一個貧窮的地方,我們應該多送一些東西給他們。」我的大腦基本上爆炸了。我設法解釋,非洲不僅僅是一個到處都是值得同情的窮人的地方。
艾琳娜:在我們離開前幾個月,我確實有一陣子在想:哇,我們真的要這樣做嗎?但整個旅程真的是天衣無縫。這太神奇了。我們只有一次在柬埔寨感到驚慌。我們搭乘一輛包租巴士,途中在一個小鎮停下來上洗手間。我讓女孩們先走,當我從洗手間出來時,我看到伊凡站在那裡。巴士不見了。
伊凡:因為艾琳娜在浴室裡待的時間有點長,我不得不做出決定。假如我和女孩們待在巴士上,艾琳娜從浴室出來時,就沒有人在場解釋巴士要回來了。
艾琳娜:是的,你說過了,我說:「下次,不要再單獨留下我的女兒們了。」[笑]我不應該笑。那是我這輩子最長的12分鐘。
莉莉:順便說一句,我不知道巴士要回來了。我嚇壞了。我們姐妹只是坐在那裡聽音樂,彷彿「我們會沒事的。」嗯,我們不會沒事的!我們在柬埔寨,在巴士上,我們的父母不在身邊,也沒有任何方法可與任何人通訊!
艾琳娜:就像我說的,有一點恐慌。但我們確實有一個計畫,如果女孩們不回來的話。我們打算雇一輛計程車去追那輛巴士。
伊凡:在我們整整一年的旅行中,這是所發生最糟糕的事。我們從來沒有遇到扒手或被騷擾。這個世界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可怕。世界到處都是善良和好心的人。不只是扶輪社員而已,我們遇到的每一個人都這樣。這段經歷真的改變了我們對世人的看法。
口述由Steve Almond撰寫
成為開放水域的游泳選手
麗杜‧凱迪亞(Ritu Kedia)
扶輪青少年交換,印度到美國佛蒙特州,2005-06年度
芭卡‧凱迪亞‧阿格拉沃(Barkha Kedia Agrawal)
扶輪青少年交換,印度到奧勒岡州,1999-2000年度

芭卡:我和我妹妹開始學游泳的地方是我們居住的印度安拉瓦提(Amravati)市運動中心的泳池。可是那時我父親在報紙上看到600公里外的孟買有一場5公里的游泳比賽。他帶我到那裡,讓我下到海裡。當時我9歲。
麗杜:芭卡參加那場比賽的前兩次她沒游完。第三次,她和我姑姑待在孟買約一兩個月,找教練練習。她的教練說:「你知道,對長泳來說,你需要很大的耐力。你必須很堅定。你需要練習。」他認為她具有這些能力。第三次,她成功游完5公里。當時她12歲。
芭卡:我第一次獨泳是在那場比賽之後幾個月。獨泳是這樣子的:那不是和其他選手比賽。你不能碰到船或是上船,否則就失去資格,可是你可以愛游多久就游多久。完成那項泳賽本身就是成就。我的第一次獨泳是36公里。我的下一場是參加瑞士的蘇黎世湖馬拉松泳賽。那是26.4公里的計時賽,選手必須在12小時之內完賽。我獲得銅牌。
麗杜:心理上及精神上,我們家及扶輪大家庭都不斷給我們支持:每次我們游泳比賽完回來,就會有20名扶輪社員帶著花束及花圈及音樂在火車站等我們。他們會邀請我們參加扶輪社例會來分享我們的體驗。
芭卡:我們在童年就接觸扶輪。我們父親基秀‧凱迪亞(Kishor Kedia)曾擔任扶輪社社長,後來還成為3030地區總監。他以前會在我們游泳的泳池舉行他扶輪社的理事會。我父親會和其他理事坐在那裡,我母親會幫我們計算圈數。
蘇黎世湖的比賽後約1年,我參加扶輪青少年交換到奧勒岡州密爾瓦基。我去看波特蘭拓荒者隊的籃球比賽。我參加《森林王子》(The Jungle Book)的戲劇演出。我認為他們給我一個角色的唯一原因是主角毛克利(Mowgli)的女朋友是印度人。
麗杜:我從青少年交換學到的最大收穫就是你心裡想的事就應該去做,否則事後會後悔。佛蒙特州的布蘭登(Brandon)是一個關係非常緊密的社區。學校裡有些人從3歲開始就成為朋友,所以我很難交到朋友。有很多事是我現在認為我當時應該做的,可是我沒有。
隔年,在2007年,我在一個月之內游了4場國際賽。我的第一場開放水域泳賽是直布羅陀海峽,從西班牙游到摩洛哥。之後是希臘的托羅尼歐斯海灣,再來是瑞士的蘇黎世湖,最後是英吉利海峽。當我泳渡英吉利海峽時,我真的已經筋疲力竭了。
芭卡:我認為麗杜可能是開放水域泳賽唯一在一個月之內參加4場國際賽的人。在她橫渡英吉利海峽後,隔天我們到協會辦公室去領證書。他們說,你們是亞洲第一對泳渡英吉利海峽的姐妹。我們不知道有這樣的記錄。我們是全世界第四對。
麗杜:我和姐姐泳渡直布羅陀海峽時,她是女選手第二名。在你下水的地方,場面很混亂,有幾秒鐘你根本不知道誰在撞你。水從四面八方而來。你會覺得你好像在瀑布底下之類的。然後你會想:「好,我們來找一種節奏,開始游泳。」
芭卡:2016年,麗杜到孟加拉,在孟加拉灣國際馬拉松泳賽締造世界記錄。她是參賽的人當中最快的,不分男女選手。可是在比賽期間她還被水母螫傷。
麗杜:我看到一球白白的東西朝我而來。有很長的觸手,感覺就像1,000根針刮過我的手。我大概失去意識幾秒鐘。超級刺痛。就像有人朝你潑強酸。引導我的船上漁夫說:「抓住救生圈,爬上船來。」可是在馬拉松泳賽一旦碰到船就失去資格。所以我說:「只要我還有意識,我就會游下去。」然後我繼續游。非常非常痛。我想我一心只想要把它游完;那就是我最後打破世界記錄的原因。我手和前臂的皮膚花了近兩個半月才恢復正常。
芭卡:在我游英吉利海峽時,天色很黑,正在下雨,風很大。英國的雨很可怕。它像是會割穿你的身體。我父親和教練告訴我要靠近船游來擋風。所以聽到那個巨大聲響時,我保持安全的距離游,可是又很靠近船隻。
麗杜:我至今仍然記得那個聲音。我在船上。大浪打來,船往下。我聽到很大的爆裂聲,我們以為船打到她的頭或是什麼。我仍然記得我父親和教練臉上的表情。他們大聲呼叫她:「芭卡!芭卡!」
芭卡:我以為他們在為我加油,像是:「衝,芭卡!衝,芭卡!」可是後來我瞭解到那個芭卡不是歡呼的口氣,而是擔憂。然後他們看到我還活著,就說:「繼續游!繼續游!」隔天他們才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麗杜:她參加的是那一季的最後一場。那時是9月。那天,她是唯一完賽的獨泳者。天氣糟透了。
芭卡:12點我看到法國海岸時,我所游的距離本該只花45分鐘,可是因為大浪我卻多花了5小時。
麗杜:你聽到很多選手說:「我差一點游泳橫越英吉利海峽。」可是沒有幾乎差一點這回事。你要不是游完,就是沒游完。開放水域是對你身為人的大考驗,因為你是一個人游。你一天練習8小時:上午4小時,晚上4小時,加上每兩星期游一次8到10小時的長泳。
芭卡:如果你想要冒險,挑戰自我,挑戰大自然,那就試試開放水域游泳。對這種游泳來說,你所做的每件事就是代表你這個人。
麗杜:它給你紀律。它給你意志力。它給你信心,因為你覺得:如果我做得到這個,我就做得到人生其他每件事。
口述由Frank Bures整理
步行橫越阿爾卑斯山
亞利山卓‧甘登(Alexandre Gandon)
法國坎城-里維埃拉(Cannes Riviera)扶青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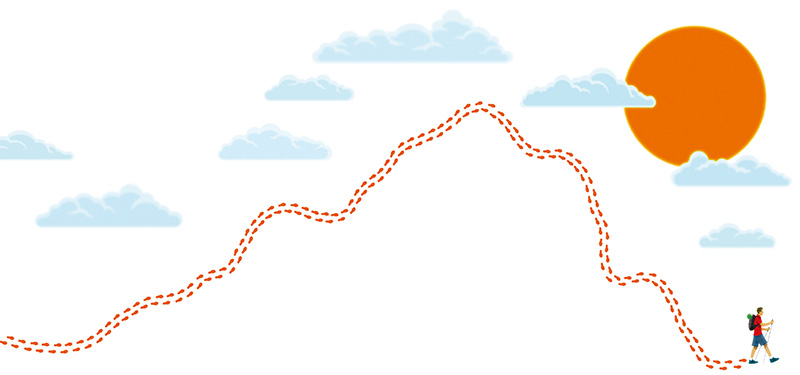
當我開始長距離健行──像是2019年我從法國南部坎城走1,500英里到丹麥哥本哈根── 我的重點從來不是體能挑戰。我只是在我的假期探索另一種旅遊方式。我覺得健行是認識人的最好方法。
2020年夏天,我決定從坎城橫越阿爾卑斯山到日內瓦。路線只有370英里,可是22英里的高度差讓它成為難度很高的任務。為了增加趣味,我計畫在星空下睡覺,所以我只帶一個小背包,空間只容得下兩雙襪子、兩件T恤、一件雨衣、兩條求生毯,以及一個手機用的輕型太陽能充電器。
我也帶一塊特殊香皂每天洗衣服用。在夏天,山區有足夠的太陽及風讓衣服很快就乾,也有足夠的湖泊和河流可以讓我盥洗── 雖然冷水會令人精神為之一振(最保守的說法)。可是健行時保持良好衛生十分重要,而且我看到人或到烘焙坊買麵包時,我想要看起來有把鬍子刮乾淨。此外,我計畫沿路拜訪扶輪社員,例如在法國布聖莫里斯(Bourg-Saint-Maurice)及安納馬斯(Annemasse)迎接我的社員。
當時,我正擔任坎城-里維埃拉扶青社的社長,所以我為這趟健行增添另一個新元素:為某個目標募款。本社其他社員協助募款及媒體宣傳等事務。我們也腦力激盪來挑選一個本地我們可以協助的組織。突然間,我的健行不再是個人而是集體的行動。我們選定「里奧組織」(Association Leo),它資助兒童癌症研究並提供經濟援助及道德支持給罹癌兒童的家庭。它的名稱來源是一個因癌症離世的15歲男孩,創辦人正是他的母親戴芬妮(Delphine)。在我健行期間,她連同她的丈夫及女兒不斷傳送鼓勵的訊息給我,成為很棒的激勵力量。
我在8月1日從坎城的節慶宮會展中心(Palais des Festivals)出發。健行穿越阿爾卑斯山並不如你可能預期的那般困難。當然,我需要做某種程度的體能準備。我做呼吸練習,強化肌肉,在出發前半年,我停止吃肉好讓自己減重,以擁有更適合健行的體態。我之前的健行也讓我準備好面對行程中可能發生的事。我習慣健行,不再會有長水泡的問題。有個有趣的差別,阿爾卑斯山步道的石頭對腳底來說並不如── 比方說── 科西嘉島的硬。後者的石頭更可能碎裂,覆蓋步道的碎石也比較尖銳。
最重要的守則是要喝大量的水,這在阿爾卑斯山區並不困難。即使我不渴,我還是把握每個喝水的機會。我決定只在沿途遇到的商店吃東西,可是我常常可能連續48小時都沒吃。在某些路段有人陪我一起走時我也會得到協助。今年擔任昂蒂布角(Antibes Cap'Azur)扶青社社長的朋友馬修‧梅羅(Mathieu Maero)頭兩天陪我一起走,其他朋友會在沿途與我會合。那時我發現就跟騎自行車一樣,如果有人走在前頭會有助於我向前走。
我沒有固定的路線。我用一個叫做「造訪」(Visorando)的應用程式,上頭可以找到健行步道的詳細地圖。可是我很想要造訪一些地標,包括阿爾卑斯山海拔最高的人工鋪設的隘口── 伊澤爾谷(Col de l'Iseran)。(環法自行車大賽的粉絲對這個地點應該都很熟悉。)我睡在這個隘口最高點附近,海拔近8,000英尺。這是我最具挑戰性的夜晚,溫度降至近華氏44度(約攝氏6.7度)。保暖的一個訣竅就是躺在用松樹樹枝鋪的床上。
絕大多數的時候,我運氣都不錯。我沒想到沿途遇到的阻礙會這麼少。唯一算是意外的一次是有一隻黃蜂叮了我的下嘴唇(我很容易「招蜂」引蝶,經常被叮。)我的嘴唇腫得很可怕,可是我設法找到藥局,嘴唇不到一天就恢復原來的樣子。它讓我學到處理挫敗時不要過度驚慌。
在阿爾卑斯山,你必須當心雷雨;如果遇到了,要遠離樹木,藏好你的步行杖以避免雷擊。健行時,我會注意天候,每次下雨我都會找個有遮蔽的地方補補眠。可是整體來說,老天爺很幫忙,我就如計畫般在8月20日抵達目的地。我們超過我們的募款目標,募得3,000英鎊,相當約3,500美元。為此錦上添花的是日內瓦扶輪社社員為我籌辦的歡迎會,他們辦理一烤肉趴來向我致敬。我必須承認,再次吃肉的感覺很棒。
口述由Alain Drouot整理
帶著自體免疫罕見疾病──以及更罕見的狗──活著
米歇爾.穆羅(Michelle Munro)
華盛頓州南惠德貝(South Whidbey Island)扶輪社

我被診斷出患有一種名為復發性多軟骨炎的自體免疫罕見疾病。這個病會讓你的免疫系統攻擊體內的軟骨及結締組織── 你的耳朵、你的鼻子、你的氣管、你的心臟。大多數人都不知道你體內各處有這麼多軟骨組織。當醫生說:「我們會替你轉診給一位風溼病專科醫師,他會幫你治療」時,我心想我可以當天看到醫生。可是其中一位護理師告訴我:「不急。不是說你看了就會改善。」
那不是我想聽到的。我是個非常樂觀的人,所以我開始盡可能多瞭解多軟骨炎這個病,可是當時的資訊比今天少非常多。我在網路上看到的每項資訊都提到診斷後壽命剩3到5年。從那時候起,我就瞭解到那是因為人們太晚獲得診斷。我非常堅信獲得良好的醫療照顧,我會比這個多活很久。
不知道是我吃的某種藥還是這個病本身讓我一眼失明。我不確定我是否另一眼也會失明,所以我開始研究導盲犬。我發現還有其他服務犬,包括適合我這種情況的。填寫申請書和面談的過程真的很困難。我自己之前都在非營利組織工作,提供他人服務,現在我是那個需要幫助的人。
我的第一隻服務犬海頓(Hayden)和我非常親密。我跟他溝通幾乎不用開口。我記得有一次我從樓梯跌到地下室,海頓跑下來查看我的狀況,可是我無法說話,因為我摔斷了幾根肋骨。海頓往樓上衝,我心想:「你在做什麼?」然後他把電話拿來給我,這是他受訓在危急時要做的事。可是我無法打電話,因為我無法說話。所以他再次跑掉。通常在那樣的情況,他會躺下來陪我。可是他跑到我們的後院不斷嚎叫,直到一位鄰居,他有鑰匙,進來房子裡,打電話叫救護車。聽到海頓嚎叫,鄰居知道有事不對勁。
我現在的提歐(Theo)已經養兩年了,所以我們還在瞭解彼此。他會做每件我需要他做的事。當我發作時,即使我太太在場幫我,無論我們在哪,他還是會跑去拿我的疼痛藥來找我。
我盡量保持樂觀,可是新冠疫情不一樣。我打了疫苗,可是因為我的病,我的做法還是像沒打疫苗一樣── 即使戴口罩是個挑戰,因為我的軟骨組織不夠堅固到可以讓耳朵上部不會往前翻起。
我在2020年夏天,疫情燃燒之際加入南惠德貝扶輪社。我很幸運,因為我的扶輪社非常認真看待防疫措施。在Zoom線上例會時,總會有人問:「提歐在哪裡?」提歐佩戴著一條扶輪頭巾,更正式的場合他還會打扶輪領結。他被提名為本社的吉祥物── 即使其他社員也會出現在Zoom畫面的寵物貓狗可能無法完全認同。
口述由Frank Bures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