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們認知的世界末日?
2021/11/29
閱覽數 1200
作者 撰文:Frank Bures
分享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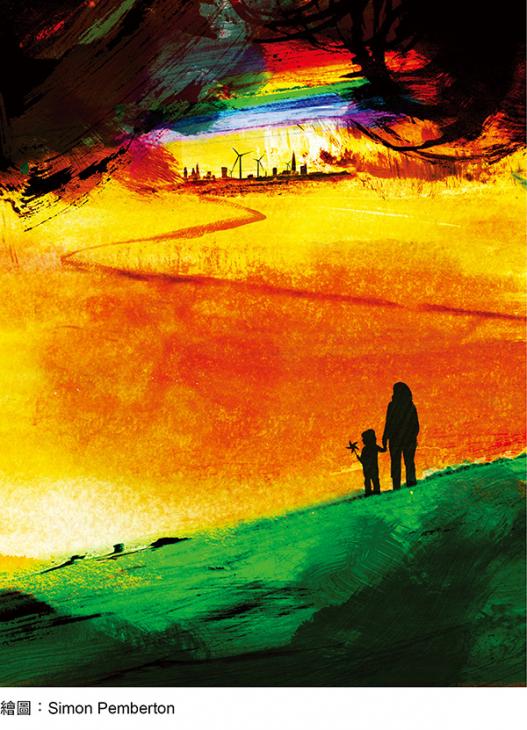
關於氣候變化的世界末日故事
並不能預言我們的命運
有天早上,我在看報紙時,看到一個令人震驚的頭條標題:「氣候變化的『紅色代碼』」。它接著說:「新出爐的聯合國報告顯示,許多可怕的影響已被鎖定;避免災難需要採取積極行動。」我13歲的女兒瞄了一眼這則新聞。
「我不喜歡我們被稱為Z世代,」她說。剎那間,我以為她在轉移話題。
「真的嗎?」我問她。「為什麼不喜歡?」
「因為這讓我們看起來像是末代,」她說。「就像我們必須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來拯救世界一樣。否則我們就是最後一代。把事情搞砸的那一代。」
「嗯,」我淡定地說,「世界不會在你有生之年滅亡。」
「但是我的孩子們呢?」她反駁。「我的孫子們呢?」
我猶豫了一下:「到時候也可能不會。」
這並不是她想要的保證,但這次談話讓我措手不及。也許我應該做更好的準備:許多父母在孩子身上看到了所謂的「生態焦慮」或「氣候焦慮」── 這種現象已經成為影響一些孩子心理健康的主要問題之一。有些成年人甚至親身體驗過。
最近發表的關於全球年輕人生態焦慮的首次重大研究揭示了這個問題。英國巴斯(Bath)大學的研究人員訪談了來自芬蘭、印度、奈及利亞和美國等國家10,000名年齡在16歲至25歲之間的年輕人。他們的發現與我自己對一名年輕人的意見調查結果類似。
在世界各地,56%的年輕人認為「人類註定要滅亡」,而75%的年輕人認為「未來是可怕的」。高達84%的人對氣候變化極度、非常或中度擔憂,39%的人說他們猶豫著要不要生孩子。作者指出,「超過50%的人感到悲傷、焦慮、憤怒、無能為力、無助和自責。超過45%的人說,他們對氣候變化的感受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和運作產生了負面影響。」
我不認為生態焦慮影響了我女兒的工作能力,但這顯然使她認為未來蒙上了陰影。難怪在一連串可怕的預測聲中,政客們宣布我們只剩下12年左右來解決氣候變化問題。
之後連續幾個星期,我一直在思考這次談話。我常發現我的思緒回到了青少年時期的恐懼。小時候,派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的「700俱樂部」有一集讓我受到輕微的創傷,該集顯示世界末日的四位騎士正在路上。在1980年代的小學裡,籠罩著我們的威脅是核戰。在大學時,我擔心「人口炸彈」隨時會引爆。然後是千年蟲、石油終有一天用完、馬雅曆法等等。
氣候變化可能與其他潛在的世界末日事件有著根本的不同。科學證明,氣候變化正在發生,人類正在推動氣候變化。但是,人類在預測一般經濟蕭條或流行病何時結束方面也沒有特別出色的紀錄,更不用說世界末日了。而且,我們有一些很好的理由可以避免末日思維和語言。
「世界末日論的問題以及我們不可避免命運的厄運和憂鬱,」《氣候焦慮實地指南:如何在變暖的星球上保持冷靜》一書的作者莎拉‧賈奎特‧雷(Sarah Jaquette Ray)說,「大多數人在心理上要麼不再關注,要麼放棄。他們絕望到很難去做什麼來避免這種命運或適應這種命運。」
氣候世界末日的情緒影響是避免採取這種心態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對兒童而言。「一遍又一遍地告訴孩子們,他們的命運是由未來 10 年發生的事情所決定的,這不僅不是真的,」雷說,「而且太殘忍了。這是不道德的。」
不該使用世界末日語言的另一個原因是,它不僅反映了氣候狀況── 它還反映了所謂的負面偏見,在這種偏見中,人類傾向重視負面資訊而不是重視正面資訊。
「急迫感和世界末日容易譁眾取寵,」雷說。「這真的很有效。在政治方面,它讓人們放棄東西。它有助於通過立法。但註定滅亡和憂鬱並不一定是我們生活的唯一現實。科學是微妙的。灰色地帶太多了,但有足夠證據顯示,很多事情正在改善,或者正在好轉,或者人們正在採取行動,我們必須堅持下去,才能抵消新聞和大腦中的負面偏見。」
邁可‧謝倫柏格(Michael Shellenberger)是《絕無世界末日:為什麼環境危言聳聽傷害我們所有人》一書的作者,他將所謂的「世界末日環保主義」與「環境人本主義」進行了對比,他把後者定義為將經濟發展和技術置於環境努力中心的方法。
在他的書中指出,許多我們認為是世界末日跡象的事情,實際上比看起來更複雜。而且,他指明有一些正面趨勢沒成為頭條標題。
「2005年至2020年間,美國的碳排放量下降了22%,」謝倫柏格說。這是巨大的。《巴黎協議》要求17%。因此,我們達成了目標,這是從未發生過的。」
雖然這種下降的一部分是由於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但疫情至少加速了已經發生的趨勢。它使我們更接近我們必須達成的目標。
「地球溫度升高時,觸發臨界點的風險就會增加,」謝倫柏格寫道,「因此,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在不損害經濟發展的情況下減少排放並盡量保持在低溫。」
儘管氣候狀況可能開始好轉,但世界末日的情境仍然有很深的吸引力。謝倫柏格指出,氣候世界末日主義反映了猶太基督教傳統的一些神話。但事實上,它可能還會更進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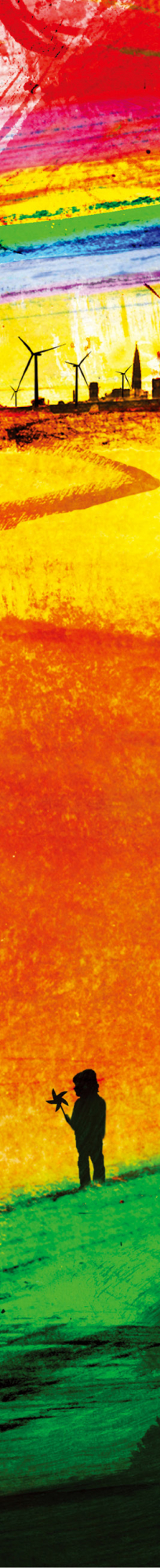 哈佛大學梵文教授邁可‧維哲爾(Michael Witzel)在他的著作《世界神話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World's Mythologies)中,審視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神話,並對比出其相似性。他發現,來自全球各地的神話有著某種共同結構,或故事:世界是在黑暗或混亂中創造出來的,然後經歷不同的時代,直到最後結束。
哈佛大學梵文教授邁可‧維哲爾(Michael Witzel)在他的著作《世界神話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World's Mythologies)中,審視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神話,並對比出其相似性。他發現,來自全球各地的神話有著某種共同結構,或故事:世界是在黑暗或混亂中創造出來的,然後經歷不同的時代,直到最後結束。通過時間和地理追蹤這些故事,維哲爾發現原始故事可能在大約40,000年前出現在亞洲西南部的某個地方,然後隨著人類遷徙而傳播到新興文化中,遠至冰島和印加帝國。
所有這些文化的神話都與維哲爾所說的「蘿拉西亞(Laurasian)」故事有著共同的情節── 以古代北方的陸地蘿拉西亞命名,許多神話都是在這塊陸地的遺跡上發展起來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故事竟然變得威力強大,並淹沒了幾乎所有的其他神話系統。世界所有主要宗教都建立在蘿拉西亞的故事之上,世界誕生於宇宙混沌,終結於爆炸,今天,世界上95%的人都贊同某種版本的宇宙混沌。
大多數人在心理上要麼不再關注,
要麼放棄。他們絕望到很難去做什麼
來避免這種命運或適應這種命運。
要麼放棄。他們絕望到很難去做什麼
來避免這種命運或適應這種命運。
當然,這些對您普普通通的13歲孩子沒有多大幫助。但是,認識到40,000年來我們一直在預測世界末日,而世界末日尚未到來,這可能會減輕一些壓力。也許就目前而言,能讓我們假設未來可能看起來不像我們的預測,這就足夠了。因為世界末日的故事和由此產生的氣候焦慮會毀了你的一天,甚至你的一生。它可能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摧毀我們的世界。
「聚焦在正面是需要付出努力的,」雷說。「這是非常困難的。這是一種訓練。但是,我們擁有做到這一點所需的所有技術。我們擁有做到這一點所需的所有科學。我們有明顯的政治和公眾意願。我們有資格在這方面做一些重要的事情。」
就我而言,我會告訴我的女兒,氣候變化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我們正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我會告訴她,希望是人類最大的可再生資源。我會告訴她,有些好事正在發生,這些好事至少和壞事一樣重要。
法蘭克‧布雷斯是《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長期撰稿人,也是《瘋狂的地理》的作者。




